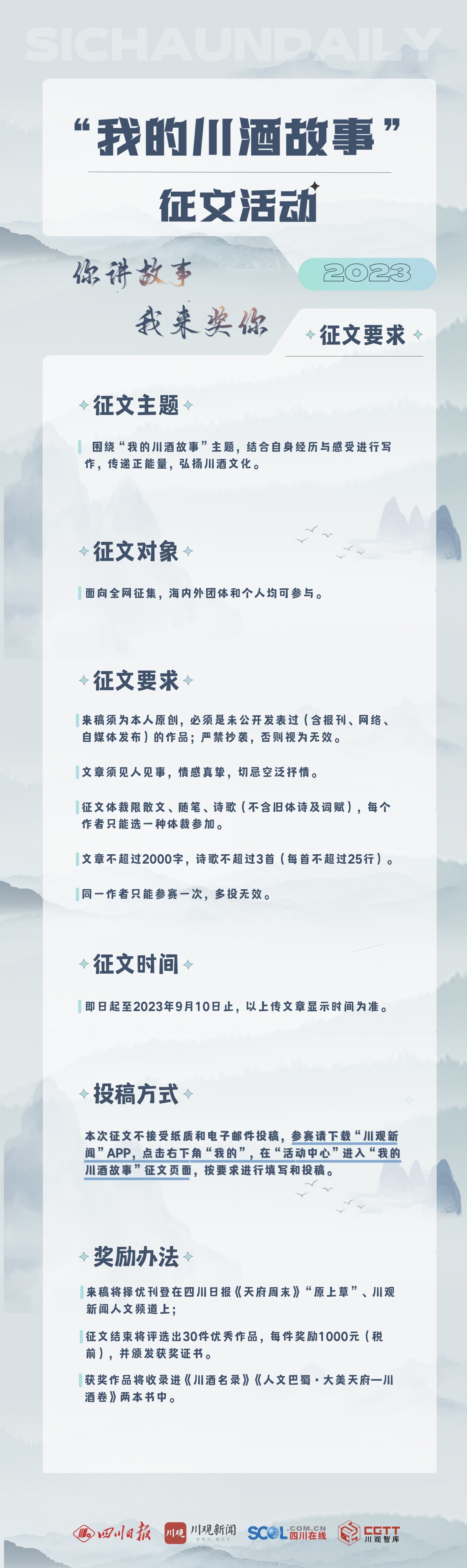杨素宏
我不善喝酒,沾酒必过敏,过敏的滋味有多难受,别人体会不到。同学、战友、朋友、亲戚聚会,因为不喝酒,我总有些尴尬,甚至感觉生活中缺少了一点人际沟通的“介质”。
我虽不善喝酒,但喜欢读书写作。年少时在家乡,中学的同伴找对象、谈恋爱,我在油灯下埋头阅读《林海雪原》《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考失败,我没有自暴自弃。在跟随父母种地的时日里,一边复习准备参加下一年的高考,一边开始文学创作。
秋收结束后,父亲去了一趟远离本村的另一个偏僻山村。回来后,让我到那个山村小学校当代课老师。“每年他们村上给三四百斤谷子作报酬,至少能养活自己。”父亲说。
我不干,就外出打工。我一边打工,一边在工作之余寻空进了当地的图书馆。图书馆虽小,却是书的海洋。我庆幸能在书海里徜徉,汲取知识的营养。阅读的同时,我还抄录下一整本《名人名言录》和一本《历史上的今天》(记述世界上每天发生的大事)。
打工的第二年,我刚满20岁,第一篇小小说《星期天》刊在1983年12月23日《云南法制报》副刊版;第一篇散文《三宝,我美丽的故乡》获得《青年时代》杂志社“我爱家乡”征文三等奖……
我来了劲儿,一边干活挣钱,一边挤时间读书写作,反复咀嚼着书中的名篇佳句,与书中的人物对话,同书的作者“隔空交流”,从书中获得创作的灵感:“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夜深人静时,我在灯下埋头读书写作。仅1984年,我就写下了小小说6篇、散文22篇,共计6万多字。
1990年春节,我由于要值班不能回家过节,同事李长华回老家过节时,顺道到我家去看望我的父母。返回时,父亲将两只装满他自酿的重阳酒(糯米曲酒)的玻璃瓶,托李长华带给我:“让我儿子在外地也能喝到家里酿的酒。”
李长华辗转1000多公里回来后,将装着酒的提包交给到农贸市场采购食材的同伴。同伴不知道包里装的是玻璃酒瓶,顺手往车厢上甩。“啪”一声脆响,酒瓶碰碎了,酒香顿时四溢。李长华和同伴四目相对,直呼“太可惜了”。
虽然没喝上父亲托李长华带来的重阳酒,但我领受到了父亲的爱子之心——让我永远铭记的父爱。
我虽不善饮酒,却一直在酒香中成长。父亲喜欢喝酒,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可以说,从我记事起,他每天都在醉酒中度过。自家酿的苞谷酒、米酒,他或自斟自饮,或招待亲朋。当然,亲朋好友送给他的酒,在他手里是从来不过夜的,不醉不罢休就是他的酒性。
父亲种田是把好手,手艺活儿也不差,木匠活做得精细,石匠活也顶呱呱。他制作的桌椅柜子,既精致又扎实耐用,附近村寨碾坊、磨坊的石槽滚子,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出自他的手。那时,他帮乡邻们打家具,大家都请他喝酒以示感谢。那些醉酒的日子,是父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1999年,父亲从乡下老家来成都跟我们小住。为让父亲尝尝高档酒的滋味,我特意花了400多块钱买了一瓶五粮液酒给他喝。没想到他竟埋怨起我来:“几百块钱一瓶,太贵了嘛。还不如把钱给我,我可以买100多公斤苞谷酒呢!”说完,他还是忍不住把五粮液倒进杯子里:“嗯,这酒好!”那副陶醉的样子,让我们哈哈大笑。
2015年秋天,父亲去世。在他的葬礼上,亲友们说:“要是他听医生的劝不再喝酒了,可能会活得更长……”我对大家说,父亲的生命与酒结缘,他活了78岁,走得并不遗憾。
人生旅途中,或多或少都会有疲惫的时候。每每这时,如有一坛醇香佳酿,邀三五好友小聚小酌,解乏消困,共品生活之美,让闲暇时光充满惬意,岂不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