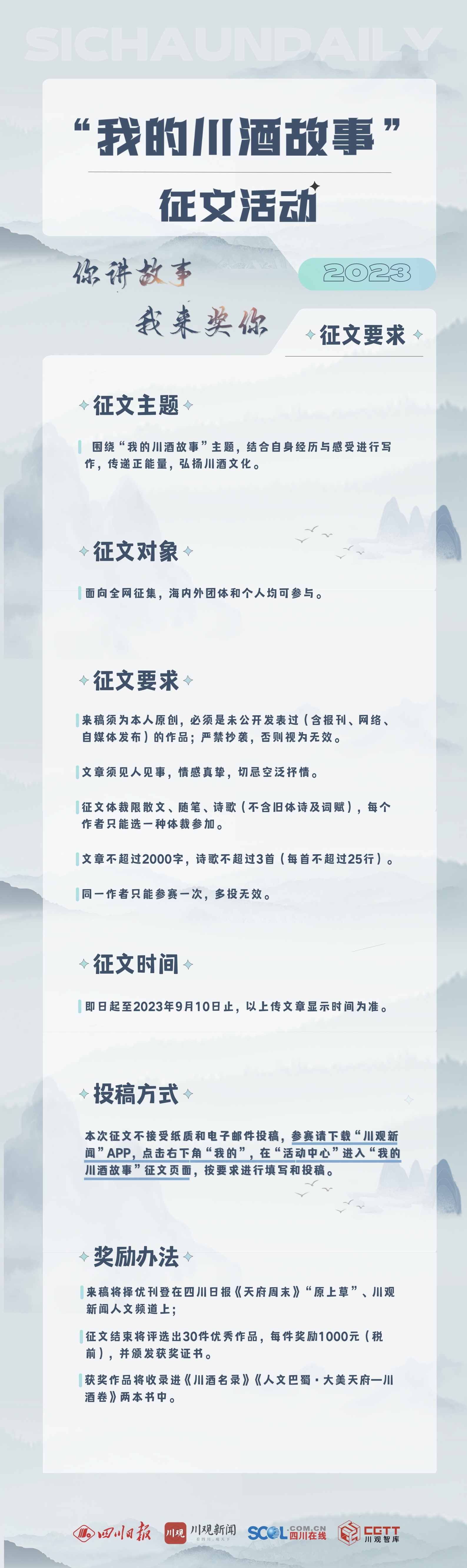夏明宇
我今年74岁。我饮用的酒,开始是地道的江津老白干,之后常饮泸州老窖、全兴大曲、郎酒、尖庄和绵竹大曲,再后来也喝喝剑南春和五粮液。可说是一辈子与川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第一次饮酒时,是为了疗伤:因为学着抬石头还不会走路,脚被扭伤了,一会儿脚踝就肿了起来。好心的邻居大叔用药酒给我揉搓了半天,又用土碗倒了小半碗老白干出来,要我使劲喝上两三口。
“我——我不会喝酒!”我轻轻用嘴唇抿了一下,感到那东西又辣又苦,于是焦眉烂眼地推辞说。
“哎呀,是喊你当药吃点儿,不是招待你——你不吃,我就一口干了哈!”大叔说着,端过碗去,果真就是“啵”的一大口,顺势还丢了两颗干胡豆到嘴里嚼着,又道:“这点酒还不够我打湿嘴巴呢!”
“就是,要恨病吃药——还不快点喝两口下去!”母亲也在旁边使劲催促。
那时候,老白干的确金贵,要凭酒票才能在商店买得到,而且每人每月就二两酒票。
被逼无奈,我只得壮起胆子喝了一大口下肚,五脏六腑顿时燃烧起来。但是,也真灵,当天晚上,脚痛就缓解许多了,肿也消了些。
我第一次喝醉酒,是1979年,正好是我的而立之年。年初,乡亲们推举我当了生产队下面的作业组组长,秋天粮食获得大丰收,黄谷和杂粮都成倍增产;同时,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也到了。
那是一个凉爽的秋夜,乡亲们在保管室坝子头摆下酒席,庆祝丰收并为我送行。这也是我平生经历的第一次“大宴”:整整20桌,每桌尖尖的一大盆肥墩墩红烧肉和一大壶新酿的美酒,我和几个年轻朋友边聊边饮,聊理想人生,聊未来的好日子,一直喝到鸡叫头遍、月亮偏西,醉得来嘻嘻哈哈地跌倒成一团,一齐滚落到保管室外面土坡下的红苕地里。
我再次喝醉酒,是1992年。那年暑假,我到北京参加一个短训班学习,南来北往的同学们一致决定趁周末凑份子聚聚,加深相互间的认识了解。但大家在聚会时喝点什么酒的问题上起了争执,有人说就地取材喝二锅头,另有人说那不如喝他家乡的汾酒。我连忙绵中有刚地凑上一句:“其实还是我们四川的酒好些,香味浓郁南北皆宜……”
“对对对,还是川酒好!”我的提议得到两位关东大汉的支持,他们甚至一口咬定川酒中的郎酒和泸州老窖都特别不错。于是,我们就在北京喝了红花郎和泸州老窖。为感谢关东大汉对川酒的认同,我有意陪他们多喝了几杯,不想便醉了,那晚连时尚的镭射电影也没看到。
我第三次喝醉酒,已进入新世纪。其时,我已届知天命之年,却因为评了职称而聊发少年狂,在同事和亲友们的祝贺声中喝了不少酒,把家中珍藏的几瓶好酒全都喝光了。别人醉没醉我不知道,我却醉得一塌糊涂,平生第一次因为醉酒到医院输液,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
“别以为评了教授就该放肆喝醉,真醉死了什么都不是!”这时,终于出了一位诤友,声色俱厉地警告我。我牢记了这次教训,此后即便再有什么大喜大悲的事情,也无论有多少好朋友劝酒,我都始终把握着度。
饮酒把握度,少饮能持久。或许就是坚持了这个原则,现在我还能小酌几口,有时也陪朋友浅饮几小杯。并且,我至今仍对川酒情有独钟,家里存放的都基本上是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