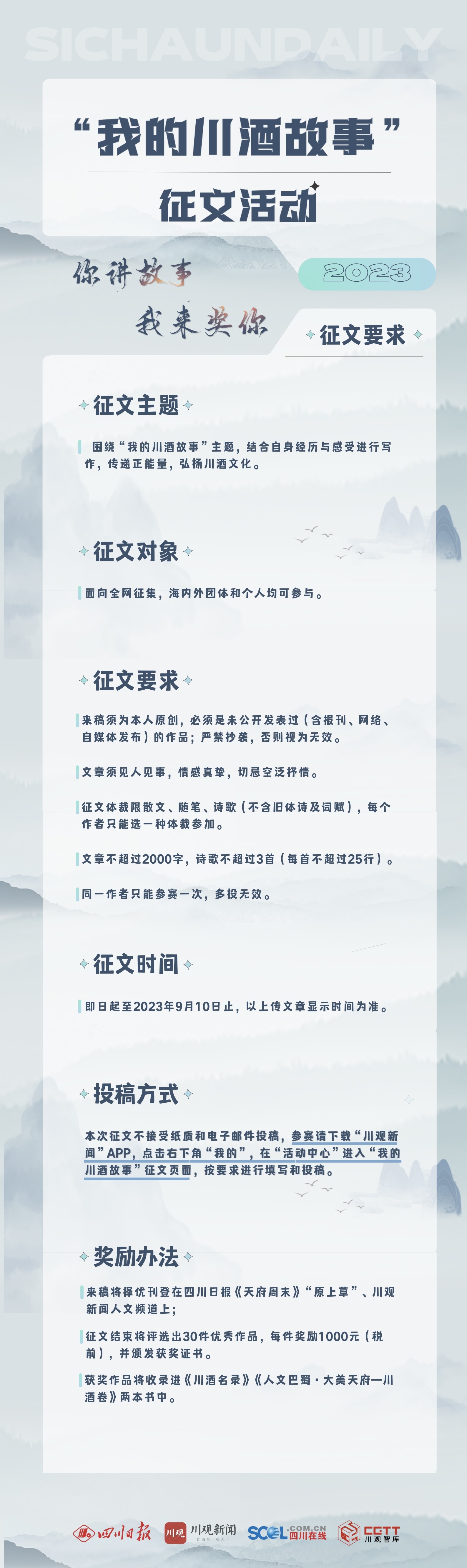廖兴友
吞云吐雾难成器,一碗川酒伴一生。少年时,我被父亲赏了一碗酒。那一赏,让我再也离不开酒,就像乳儿离不开娘,游鱼离不开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老家——龙泉山脉成都东山五场之一古廖家场,只有一个小酒厂。父亲有腿疾,一到阴雨天气膝关节就疼,别说干农活儿,走路也难。说来也怪,父亲喝上一两口苕干酒,关节疼痛很快就好了。
我脑子笨,每遇考试,语文满分,数学不及格。父亲认为我不是读书的料,家里缺劳力,叫我老实在家干农活。从此,我一头扎进旱地,翻土薅草,播种浇灌,收割玉米、小麦,挖窖红苕,晚上读书识字,开启了“半工半读”的日子。
我18岁生日那天,一如往常。虽然家里摆了两三个荤菜在桌上,可我从早到晚挑粪桶双肩红肿,酸疼难忍,毫无生日的喜悦。
母亲把在供销社打的散酒给父亲倒了一碗,这酒是母亲用晒干的红苕片换的。我家旱地多,盛产红苕,人畜吃不完,又担心开春烂掉,几分钱一斤卖又可惜。母亲勤快,稍有闲暇,就把红苕洗净,切成薄片暴晒,干脆了,装袋储存,想吃苕粉了,拿苕干换。家里白酒快喝完了,也拿苕干换。
廖家场东。井里的水是龙泉山上浸透来的。廖家场小酒厂酿酒,是取岳庙边一口古水井——凉水井的水,用这水井里的清泉酿出的酒不用添加香精什么的,喝一口,打的饱嗝都要香几条大街。母亲一年晒干的苕片有1000多斤,能换好几百斤白酒。我想,父亲娶了我妈算有口福,一辈子没少喝酒。
父亲似乎感觉一个人喝酒特没劲,问我要不来一碗。我摇头说不:“喝酒是你们大人的事,我才不喝。”父亲说:“你今天满18岁了,长大了,可以喝了。”
这时,从隔壁邻居泥巴墙缝隙里传来一段熟悉的电视广告声:“月儿明,月儿亮,月光照在酒瓶上。遂州酒好没法说,不喝硬是睡不着……嫦娥姑娘下凡来,硬要和我喝一台……”这酒怎会如此神奇,搞得嫦娥也神魂颠倒?
当年在四川电视上“霸屏”的遂州酒,是我最早看到的酒类电视广告。母亲似乎被隔壁的电视广告所感染,没经得我同意,就给我倒了半碗:“父亲叫你喝,就喝吧,先来半碗试试,看受得了不。”
我放下饭碗,端起酒碗,闻了一闻,味浓烈。伴随着浓烈的,还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醇香。我不容分说,敞开喉咙就喝下去一大半。第一次喝酒,酒的烈性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被呛得眼泪直流,但难受很快被温热醇香取而代之。那夜,我睡得很熟,偶有打嗝,酒香满屋。
我当时也算是文学青年。19岁生日那天,来了二三十位五湖四海的文友。我把积攒的钱买了40瓶1.8元一瓶的沱牌酒作为主打酒,买了一瓶31元的东西60°莲花瓶剑南春,一瓶50元的白麦穗瓶52°五粮液;一瓶46元的60°白方瓶泸州特曲。五粮液、剑南春、泸州特曲是当时川酒的“天花板”。
酒好不怪菜。有了美酒,大伙儿对吃什么也就不太在意了。因此,下酒菜主要就地取材,如自家种的花生、蚕豆、豌豆,一炒一煮一蒸,外加几斗碗猪头肉,那气氛完全不输满汉全席。
沱牌瓶装酒喝过三巡,我再拿出“天花板”,请大家限量品尝一口。文友们晓得只能品尝一口,喝到嘴里,久久不忍下咽,慢慢感受着川酒独特的魅力香味。从福建来的文友小尤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白酒,也是一次性喝过最多品牌的川酒。”
入蜀不喝川白酒,等于没到天府走。北纬30°的四川盆地,终年恒温恒湿,土壤肥沃,为酿造美酒提供了独特的地理环境。天府之国优渥的农业经济,为孕育发达的酿酒业提供了基础保障。泸州、宜宾、绵竹、邛崃四大白酒产地,“六朵金花”组成的川酒方阵所占据的不仅是我国白酒市场的半壁江山,香醉的不仅是中华大地,还有五湖四海的地球村。
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偶有出省、出国,我总是习惯性地以川酒作伴。后来,我发现,无论是省外还是国外,处处可见川酒。滋养我味蕾,融入我骨子灵魂的川酒,哪里需要随身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