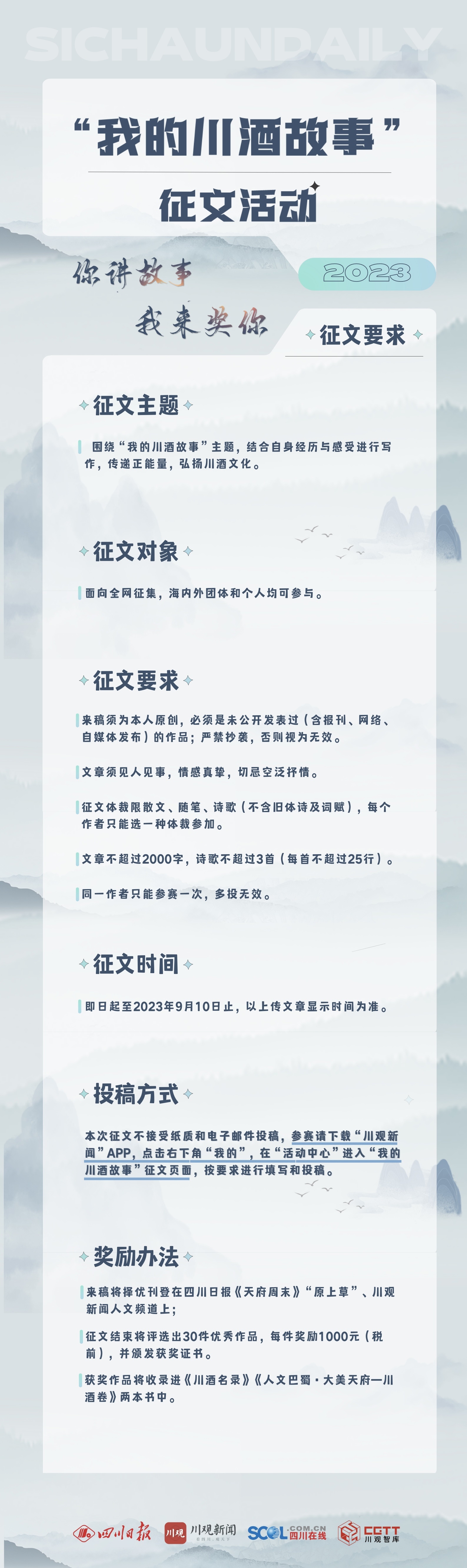林佐成
那年夏天,朋友来电说,他有一个酿酒的朋友想找我聊聊。
我刚到约定的茶楼坐下,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随朋友走了进来。中年男子模样憨厚,个儿墩笃,黝黑的皮肤配上灰色的体恤,倒与乡村酒老板的身份相符。“你读过高中吧?”被朋友称作魏总的男子刚坐下,我便好奇地问。“他是研究生毕业呢!”“研究生?”我陡地一怔,“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拱着手,一脸羞愧。“没事,没事!”魏总摆着手,憨憨一笑。
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放弃省城工作,回乡下酿酒,听起来怎么都有些天方夜谭。
魏总说,他家酿酒始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说完,他翻出手机上拍的“八庙:城北二十五里,村人谭福馨捐修,工竣遂自披剃此。康熙末年事。今住持皆缁党”的字样,“这是新宁县志《道光十五年·卷四》上的内容。”他补充说。
我迅速浏览完手机上的文字,愣愣地望着他。“我妈姓谭,谭福馨是她先祖。”许是看出我的疑惑,魏总解释道。“当年,湖广填川,谭福馨拖家带口从湖南零陵辗转来到新宁县(今四川开江县)永兴场谭家冲。他利用酿酒手艺建起酒坊,生产利通老窖获利后,建起了家庙——八庙(供奉谭姓史上8个名人)。随后,他召集家人,宣布两个重要决定:一是家庙住持须是宗族德高望重之人,二是用酒坊收入供养家庙,家庙不倒,酒坊长存……”
魏总如数家珍,说谭家先人谭吉朝、谭天林如何谨记先祖遗训,用石缸、紫砂瓦缸等盛了老窖,藏于地下,躲过肆虐新宁8年的战乱;外公谭秀才如何凭着高超的酿酒技艺,在公私合营时成立的永兴酒厂做掌脉师(酿酒第一技术指导),小心呵护着老窖品质;从小在酒厂长大、对老窖一往情深的母亲谭秀芬,如何在酒厂推行承包时,挎着筹措的10元一张沉甸甸的10万元现金奔赴现场,一次次举起“500”竞标牌子,最终获得承包权;又如何不顾母亲反对,打破“手艺自古传男不传女”的老规矩,与众多姊妹签下苛刻条约,赢来传承、经营权,然后把酒厂搞得风生水起,以致永兴乃至县城都知道有个谭金芬酒厂,再然后……听着魏总侃侃而谈,我感觉走进了一个奇幻迷离的世界。
“魏总,省城机关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你竟然……”趁着魏总喝茶的间隙,我一脸狐疑地望着他。“都怪那些酒坛酒缸酒窖。”魏总叹口气,说起了外公临终前躺在凉椅上叫声“金芬,有人打酒”咽气的不舍,说起了母亲因帮助姊妹掏空了家底以致酒厂一蹶不振的凄惶,说起了因母亲年岁渐长酒厂面临倒闭的绝望。
“我是闻着酒香长大的,实在不忍心让它倒下啊!”听着魏总动情的话语,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个面目黧黑的男人,除了担当,更蕴藏着一股无人能撼动的力量。
我是三天后来到魏总淙城老窖(辞职回家第三年注册的商标)酒厂的。我参观完规模不大却充满古旧气息的酒厂,目睹了存储数百坛老窖的地下窖池,观看了控制室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起的对酿酒全程追踪的视频,随后走进陈列室。
墙壁上,一张张展示酒厂历史人与物的黑白褪色照;橱柜里,一个个酿酒用的发黄发黑的老旧器具。魏总说,这是装了发酵液(臭黄水)从湖南带过来的母罐,那张泛白纸片是当年母亲为获得传承写下的条约;这两个笆篓似的器具是外公过去送酒用的大酒篓,那把珠子残缺的是母亲多年前用过的算盘……一段久远的历史,一种古朴的沧桑,扑面而来。
就在这当儿,一位60多岁的女人笑容可掬地走进来,我猜她就是魏总的母亲谭金芬,热情地叫了声“谭妈妈好”,竖起大拇指,直夸她能干。“快别说了,快别说了!这些年,为了这个酒厂,只差没把命搭进去。叫他不要离开成都,他偏要辞职回来搞这个。那些嚼舌的邻居,把人都气死,说他犯了错误遭开除了,说他……”她伸手指着自己的脑袋。“妈!”魏总叫了声,谭妈妈摇着头出去了。
再次走进淙城老窖已是两年后。此前,因彼此欣赏,我与魏总成了朋友,相谈甚欢。从交流中得知,自接手酒厂业务后,他一直在默默努力:筹措资金,翻新作坊,改建灌装车间、窖池;跟随老师傅选料、泡粮、蒸粮……全面掌握酿酒工艺。自考取国家一级品酒师,注册淙城老窖商标,全面提升老窖品质,占领本地市场后,又借助网络平台,利用直播带货、社群营销、网民打卡等方式,开疆拓土。淙城老窖开始引起关注,成功申报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是陪市报的记者一起来到淙城老窖的。他们参观完酒厂,直感慨酒坊历史的悠久,感叹谭家数代人对酒坊不离不弃的呵护,更惊叹魏总放弃大都市安逸的小日子,回到偏僻的乡下守护这坛老窖。
他们是在采访完魏总后接着采访谭秀芬的。“你们不晓得,他刚回来时好造孽哟,为节约几个钱,他自己翻修作坊,一根横梁突然掉下来,重重砸在右手臂上,手臂当即骨折……”谭妈妈话没说完,已伤心得哭起来,柔弱的样子,就像风雨中的小草。听着谭妈妈的哭声,我悄然将头转向一边。
或许,正是因为数代人的呵护,一坛老窖才不断散发出灼灼酒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