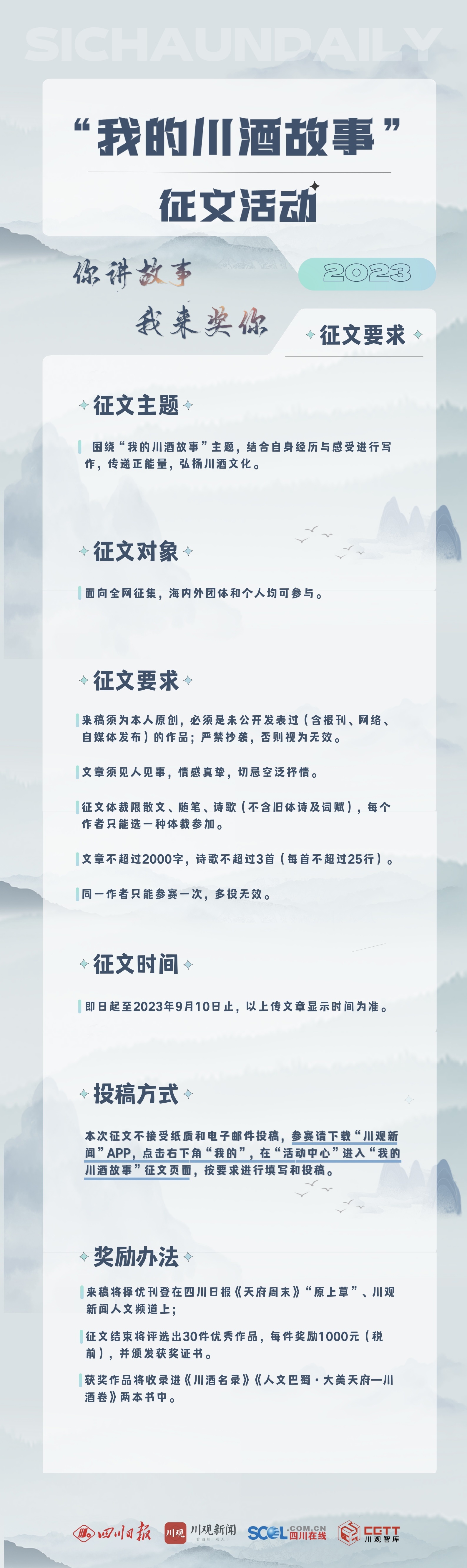陈利民
至今,我虽记不住钟叔的全名,但记住了他随身携带的酒壶,那是半新半旧的一个军用水壶。钟叔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们一同参军入伍,一同跨过鸭绿江,又一同回国参加工作。因我祖辈几兄弟都是厨子,所以父亲在战场上只能拿着锅铲,钟叔则扛着枪。
父亲和钟叔回国后,被分配到大巴山区修铁路。在工程队,父亲任伙食团团长,钟叔任掘进班班长。钟叔一脸络腮胡子,大家都喊他胡子班长。那时我年少,常常听职工家属们议论他:“这个五大三粗的大胡子干活不要命,喝酒也同样不要命。”
也许,喝酒在我的印象中缘于钟叔。
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生活艰苦。钟叔酒壶里只能装满散装的、廉价的红苕酒。发了工资那几天,他眉飞色舞,喜气洋洋,酒壶里一定装满散装的、品质较好的高粱酒。他可以一包炒胡豆或一袋炒瓜子,就喝上半壶酒。父亲曾经叹息:“他呀,在工地上干活无话可说,下了工地就离不开酒。一喝就刹不住车,没得一斤两斤下肚,不会抬屁股笑眯眯地走人。”
父亲除要照顾几百职工家属的日常生活,还要照顾来往的客人。招待客人常常喝的是瓶装泸州大曲或泸州特曲。父亲不善饮酒,只是保管酒,或者说保管喝剩下的酒。新的一批客人到来,不可能喝剩酒。父亲只好将剩酒提回来泡咸菜,母亲则将空酒瓶插一枝野菊花。
那几年,钟叔挎着空酒壶隔三差五来我家串门,摸着我的脑袋:“我来看看大侄子长高没得。”其实,他觊觎父亲提回来的剩酒。父亲拿出一瓶粘着灰尘的尖庄酒,款待老战友;母亲则给他油酥一盘花生米。
钟叔美滋滋地喝酒,父亲陪着喝茶,母亲在一旁打毛线。他每次在我家喝酒,都会拉住我,让我坐在他的腿上,把酒杯送到我嘴边说:“大侄子,陪你钟叔抿一口。我给你讲一讲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我屋头那几个丫头片子,见我喝酒都躲得远远的。”
母亲安慰他说:“老钟啊,你以后女婿多,上门拜见老丈大人,还会缺酒吗?”钟叔临走时,满面红光,心满意足,酩酊大醉。他拍拍空空的酒壶,遗憾地对父亲说:“老陈啊,啥子时候我的酒壶里装满泸州大曲,死也闭上眼了。”
有一年,工程队掀起建设高潮。钟叔带领掘进班克服困难,日夜奋战。按他的说法,握着钻机就像握着冲锋枪,过瘾!那次,他们打隧道“月掘进速度达500米”,受到上级嘉奖表彰。领导给他戴上大红花,问:“大胡子,此时此刻你有何感想?”他不加思考,脱口而出:“我想喝泸州大曲。”领导呵呵大笑,爽快地说了两个字:“管够!”
钟叔因工伤而亡是第二年秋天的事。据父亲说,那次,掘进班一个年轻人上班忘记戴安全帽,工地离家属区又远,钟叔将自己的安全帽戴在年轻人头上。当天下午,隧道喷水塌方,大小石块砸下来,钟叔的头部严重受伤。
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他紧握着一位工友的手,艰难地笑着说:“要是有泸州大曲喝几口该多好,脑壳也不会这么痛了。”说完,已不省人事。
父亲说,在安葬钟叔时,有那只半新半旧的酒壶陪伴着他,酒壶里装满了泸州大曲。
钟叔毕生唯一的奢望就是能喝到好一些的酒。对今天丰衣足食的生活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虽然时不时喝到好酒,但在内心深处总会泛起淡淡的哀愁,微微的酸楚。至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喝到好酒,我就会想起钟叔,想起钟叔那半新半旧的酒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