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姗姗 综合报道
1933年农历腊月十五,乌云笼罩着上海,一场秘密会议突然被冲,一半与会者被抓。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众目睽睽之下,一场事先张扬的转移险战就此展开……2022年4月,作家孙甘露携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重磅回归。小说一经出版,就被读者、评论界追光关注,更是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的殊荣。
多位作家和学者看了《千里江山图》后认为,这部新作是将主题叙事提升至全新文学高度的作品。作家马伯庸对《千里江山图》呈现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肌理,特别是找到了理想主义者这个群体表示赞赏,认为孙甘露展现出了极高的小说技巧,“气势磅礴、结构精巧,几笔勾画出一个时代的肌骨、几个理想主义者的魂魄。”
《千里江山图》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它的过程。孙甘露捏土为骨,化泥为肉,将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理想主义者,重新聚起他们的精神和血肉,于焦灼乱世中躬身入局。他们是父亲,是爱人,是兄弟,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测的航程。孤寂的至暗时刻,一个人看到什么,愿意看到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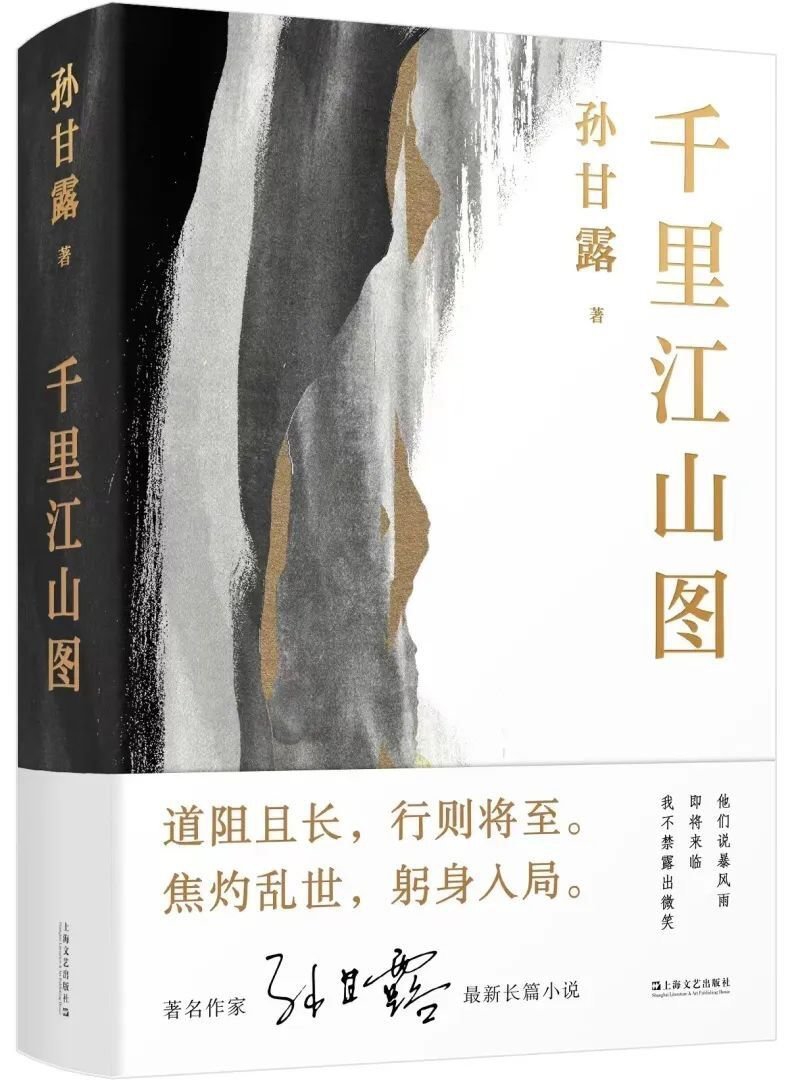
视这次写作为全新的学习过程
孙甘露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成为作家前是一名邮递员。1985年,上海市作协举办青年作家讲习班,26岁的孙甘露成为其中一员。讲习班结束后,每人要交一篇作品,孙甘露交出了《访问梦境》。这篇小说第二年在《上海文学》发表,随即引发热议:这篇小说特别不像小说,是富有语言实验性的作品。此后,孙甘露和余华、残雪等人被称为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2004年后,孙甘露不再发表新的小说,直到《千里江山图》。
昔日的先锋作家为什么要写一部名为《千里江山图》的谍战小说?
孙甘露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透露,《千里江山图》的故事来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2020年,一个契机让孙甘露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初非常秘密的一个转移行动——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距离有1000多里,但在当时,必须绕道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如此就是3000里。这是历史上非常秘密但又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中央有关领导必须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绝密地下行动由此展开。忠诚与背叛、潜伏与行动、计谋与意外、搏斗与杀戮、审讯与酷刑、阴谋与爱情,谍战元素应有尽有。
《千里江山图》正文34章,全书24万字。整部小说节奏极快,情节密度高,语言动感强,形成一种激情美学叙事的动态结构。同时,隐蔽战线里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跃然纸上,他们的身影出没在上海、广州、南京的市井街巷,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测的航程。
孙甘露坦言,《千里江山图》是他接触的一个全新的小说领域。从头至尾,他都视这次写作为全新的学习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辨析,也是对历史题材写作的辨析和想象。
小说真实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广州、南京的社会环境、市井街巷、风物百态,复刻了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最大可能地还原了中国近现代城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联系,在当代原创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将“千里江山”宏阔背景和“万家灯火”微观视角融入主题创作。
据《文汇报》报道,孙甘露在广泛搜集中共党史早期史料的过程中,参考了当时的城市地图、报纸新闻、风俗志等材料。为了文本中一处“船进吴淞口”的表述,他精确查证当时的上海水文资料后才落笔;作为背景描写卡尔登戏院上映的电影,也是通过查阅当时《申报》广告得来再化用;原文有一处关于“寒假毕业班”的描写,他从储存的创作资料包里找出“修业证书”和“格致公学”成绩报告单,供出版社编辑把关参考。
写作者的使命是要复活这个世界
谈起《千里江山图》,孙甘露说:“从写法和故事本身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像个初学者一样,进入小说,进入历史。也许,就因为这样,历史得以重新展开,对一个小说作家而言,这更意味着需要进入人物的内心。他的内心成为行动的力量,历史也是这样打开的。”
历史和故事,说起来语义的指向有点不同。历史指向某种真实性,至少是一种真实的期待。故事更像是一种讲述,一种与生俱来带有修辞性的表达,讲述和表达的方式成为小说的外貌。对小说家的考验在于,要讲得和写得像真的一样,至少让读者感觉像是真的。于是,故事成了历史,历史在故事中复活。这就是文学或小说的朴素功能。“批评家喜欢说历史在文学中重新诞生。我没把握说,这也可能会是读者在《千里江山图》中感觉到的阅读体验。”
《千里江山图》的写作过程,让孙甘露重新回到经典作家的世界中,写出了深刻的历史和人的世界。“我举例说,我会时常想到荷马、莎士比亚、布莱希特、萨特、卡尔维诺、康拉德等,幻想着他们忽然现身在上海的街头,这座我熟悉又陌生、充满着感情的城市。写作者的使命就是要复活这个世界。复活也是想象未来。从历史看取未来,就会与现实重叠。”
这是一个大时代,小说家正逢其时,躬身入局。也正因此,孙甘露意识到了自身的限制。面对的是全新的历史和现实,一切都需要重新打量和磨合。既往的经验既是财富,也许也是一种约束和负担。历史需要从现实重新出发,作家更要在世界文学之旅中找到自己的驻足点。
“粗略地回望这本小说构思之初的各种设想,似乎是想寻找小说艺术的某种本质性的力量,来和它所想表达的主题的严肃性形成呼应;或者因其隐秘错综的人物关系在全知叙述和受限的视角间寻求平衡;由于故事所呈现的机密行动和社会环境、公共空间和私人感情的交互影响,我不得不思考勒卡雷式的侧写甚至计算机式的算法,并通过明确的延宕获致精确的路径。”孙甘露说。
孙甘露试图以简约的方式回溯复杂性,或者套用詹姆斯•伍德的说法:“学着以一种隐秘且反向的方式来阅读它们,逆着它们自己的纹理刷过去。”这里的“它们”,既是历史素材,也是结构作品的过程。


孙甘露获奖感言
一直都有一种初学者的心态
感谢茅奖评委的肯定和鼓励,能和这么多优秀作品一同参评,已经是莫大的荣幸。
《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发生在90年前、1933年的上海。那一年,茅盾在上海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允许我借此向这位前辈作家表示敬意吧。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我们有幸在这里生活、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犒赏了。
从酝酿、构思、采访、查阅历史材料再到动手写作,《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对这段特殊历史的学习,也是对文学创作、小说写作的重新学习,既是对历史的再认识,也是对文学创作的再认识。
书中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年代,以及从那时延续下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通过这次写作,我对它们都重新进行了回溯。从冯雪峰、巴金、夏衍、柯灵、罗洛到王安忆,他们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写作回望历史。
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认识也因为写作而加深了。100年来,这座城市发生了各种事件,我在准备阶段了解和采访到的那个年代的故事,远比我写出来的要丰富精彩得多。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会再次讲述这些故事,它们一直在我脑中回旋,让我难以忘怀、难以平静。
所以,不管是从具体作品的写作来讲,还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写作来讲,我一直都有一种初学者的心态,这种心态促使我不断地去尝试和探索。对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的写作者来讲,这是非常有益处的。学习是伴随我们一生的,不管是广义的学习,还是关于小说写作技艺的学习,我们每天阅读和写作,就像一个乐手每天读谱和练习,这个过程实际上也伴随着对技艺的思考。我觉得,这是伴随一个写作者一生的功课。(据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