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姗姗 综合报道
一桩凶杀案让女警察冉咚咚穷思竭虑,追查真相的她同时陷入婚姻的迷局。小说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在案件与情感的复杂缠绕中,揭开一个个人物的身份、人格、心理,直抵人性最真实幽深处……在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的角逐中,作家东西凭借长篇小说《回响》获奖。这是东西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后,再次斩获文学大奖。
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是最早评论东西小说的评论家,他说东西的语言是“刺在黑缎上的大花”。“东西是一个写到东必定写到西、写到西必定是看着东的小说家。东西写《回响》,就是写的这至近、至远,至亲、至疏。”
李敬泽认为:“《回响》是对人性、对人的当代性有话说、有发现的,同时又是用小说家复杂的、反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部小说。它几乎可以构成现代经验的一个复杂但又极具洞察力的寓言。《回响》是现代以来不断地在我们的文学中、在世界文学中反复回响的关于人性和人类境遇的基本主题在当下最新的、有力的,同时又是有效的洞察和一份回响。对小说艺术来讲,尤其对现代小说艺术来讲,人性的复杂性尤其需要艺术创造的复杂性来确保和照亮。在这个意义上,《回响》是值得反复阅读,也值得深入研讨的一部作品。”
东西被认为是60后实力派作家之一,小说语言简洁精炼、准确圆融。《回响》是他继《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之后的第4部长篇小说,写作耗时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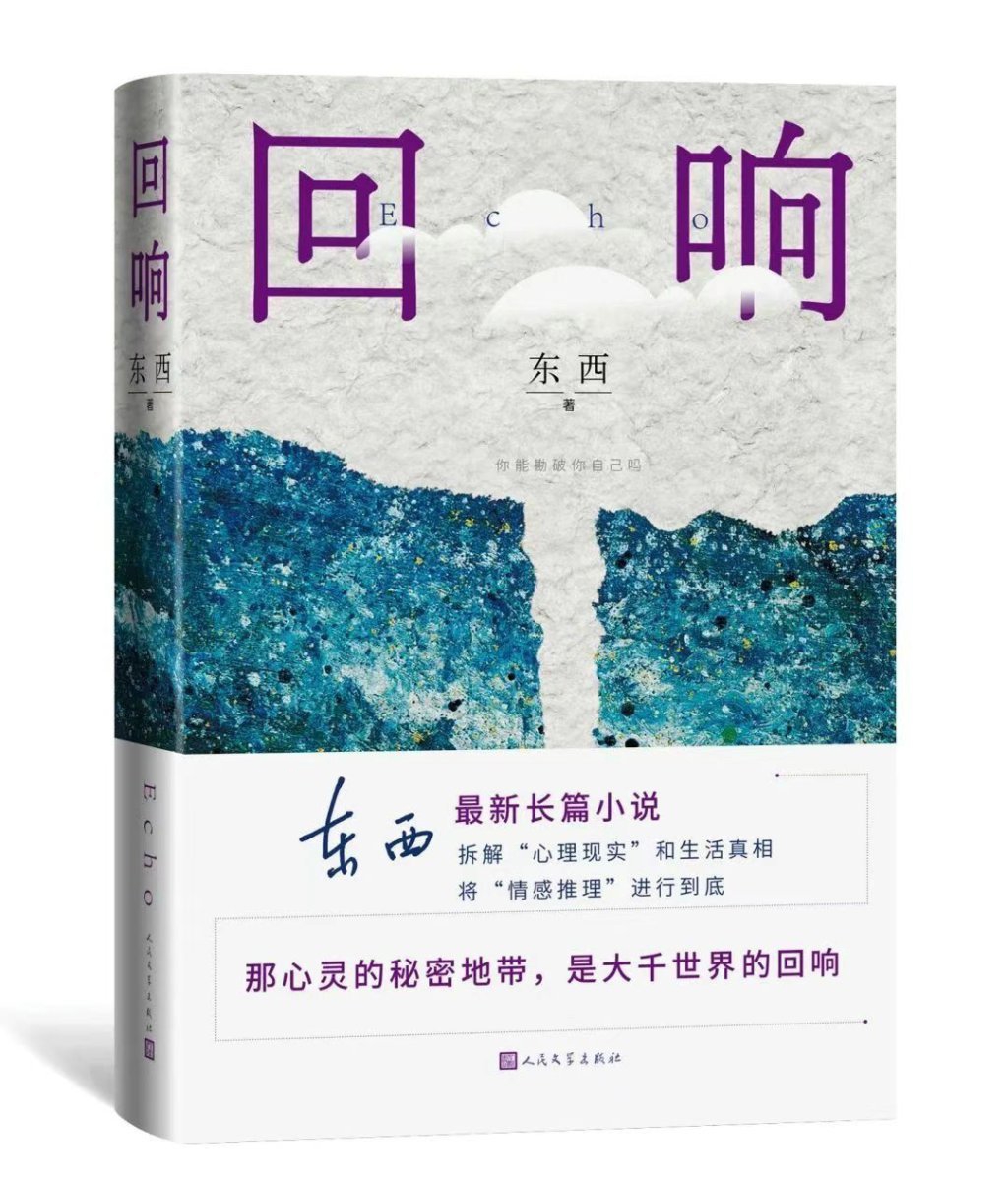
拥有更为客观和深刻的书写
1996年,东西以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惊艳中国文坛,是继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小说作家后的重要作家之一,与毕飞宇、韩东、邱华栋、徐坤、李洱、艾伟等被评论界称为新生代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是新生代作家中率先“走出八十年代”的新文体典范。
很多人对“东西”这个笔名感到好奇。对此,本名田代琳的东西曾回应说:“当时开始写作时很年轻,就像现在的网络作家,都愿意取一个好记、还有点调皮的名字,后来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在《回响》中,除保持东西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外,还拥有更为客观和深刻的书写,也多了一份对人物和现实的深层理解,其可读性超越了东西此前的任何一部作品。因为东西对每个人物的心理都进行了深挖,所以,有评论家把该作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
谈及《回响》这部新作,东西直言:“我想写的是,其实,平凡的生活就是最浪漫的生活,有时候我们是自己把它搞复杂了,但实际上可能越平凡越浪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主旋律的作品,写一个警察战胜那么多困难,她要战胜案件的迷局,还要战胜丈夫出轨的迷局,还要战胜她心理上压力大、有一点精神压力的难题。她要战胜3个难题,最后把凶手绳之以法。她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说到这部小说的创作情况,东西在《回响》后记中说:“我构思这个小说并开始写它,以为乘着一股冲劲儿会很快把它完成。但是,只写了几千字我便遇到了阻力,才发现写这个题材我还没准备好。从家庭或从案件写起?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它折磨了我好一阵子。”于是,东西不得不写了两个开头,试图二选一。他认为有两个开头就对得起这个小说了,不料这仅仅是开头的开头。
从2017年初春到2019年夏末,东西都在写这个小说的开头。一边写一边否定,一边否定一边思考,好像患了“五千字梗阻”,即每次写到5000字左右,就怀疑这不是好的开头,便习惯性地想要从头再来。
他甚至怀疑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不是故意要那样写,而是因为写不下去了才不停地只写开头部分。当然,卡尔维诺有漂亮的借口:“我很想写一部实质上只不过是‘引言’的小说,它自始至终保持着作品开始部分所具有的那种潜力,以及始终未能落到实处的那种期待。”可是,东西找不到借口,而且他也不能重复别人的借口。
下笔如此之难,是因为东西对小说涉及的两个领域推理和心理比较陌生。之前,他从来没碰过推理,也从来没有把心理学知识用于小说创作。但这次,他想试一试。“显然,这两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储备都不够。”
对人物的复杂性有了更多包容
2017年下学期,作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的东西,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聘为驻校作家。他在校园里一边写小说的开头一边构思,一边构思一边利用空余时间阅读和聆听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学习心理学对我是一次拓展,虽然那半年小说创作的进度略等于零,可我的一些观点却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尤其对他人、对自己都有了比从前稍微准确一点的认识。”
内心的调整,让东西写人物时多了一份理解,特别是对人物的复杂性有了更多包容。多年前,他在写《后悔录》时,就有意识地向人物内心开掘,并做过一些努力。这一次,他想做得更彻底。
认知别人也许不那么难,难的是认知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在认知自己,作者通过写人物得到自我认知。“我们虚构如此多的情节和细节,不就是为了一个崭新的认知吗?世界上每天都有奇事发生,和奇事比起来,作家们不仅写得不够快,而且还写得不够稀奇。因此,奇事于我已无太多吸引力,而对心灵的探寻却依然让我着迷。”
卡夫卡说:“巴尔扎克带着一根手杖,上面有这样一句格言:‘我冲破每个障碍。’而我的格言宁肯这样:‘每一个障碍都使我屈服。’”这是卡夫卡的自我心理暗示,他认为自己是个弱者,没有巴尔扎克那么强悍。有人喜欢巴尔扎克,有人喜欢卡夫卡,写作者都在找自己的同类。
对此,东西认为:“两种心态如果自我认识不足,都可能给写作带来负面影响。强者的写作心态会被自我捧杀,容易让写作变得简单粗暴;弱者的写作心态容易自我沉沦,会让写作变得犹疑徘徊。但每一种心态的形成都不是天生的,它跟家庭、现实和经历均有关系。我一直是弱者心态,犹疑徘徊如影随形,甚至经常怀疑写作的意义。”
为了克服这种心理,东西在写作过程中重读了4部经典名著,一是吸取这些作品的创作经验,二是通过阅读它们树立信心。由于过多的自我怀疑,东西形成了写作的自我预警,每天超过1000字就会停下来重读,找错误缺点,补细节。有时,写着写着,突然不想写了,停下来思考两天,发现排斥的原因要么是人物把握不够准确,要么是情节推进不对。“总之,一旦产生排斥情绪,我就知道困难降临,必须让障碍屈服。卡夫卡的写作心态有利于作品构思,巴尔扎克的写作心态有利于小说的推进。”
在2021年的钟声敲响前,东西完成了小说初稿,之后又用40天时间进行修改、校正。小说首发于《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单行本,随后获得诸多奖项。


东西获奖感言
获奖对写作一定有帮助
很高兴获得茅奖,感谢评委们的支持。
30多年的写作经历,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除了坚持还是坚持。每次写长篇小说写到最后,感觉拼的都是毅力。因此,我认为这次获奖是对我“坚持”及“毅力”的肯定。
1998年,我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幸运地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当时还年轻,并不觉得文学奖有那么重要,甚至觉得自己还可以写出更多的比获奖作品更好的作品。一晃25年过去,才发现突破自己并不容易,而要获得文学大奖,何其难也。是的,写作并不是为了获奖,但获奖对写作一定有帮助,尤其是对像我这样一根筋的作者帮助更大。
一根筋就是写作的执念,从决定吃写作这碗饭开始,我就常常提醒自己:你写的作品有意思吗?它是别的作品的重复吗?拜托,别只讲故事,能不能有点新意?这些问号一直伴随着我,一直伴随我在电脑键盘上敲击完《回响》的最后一个字。不信,你也可以试着读几页,真的和我过去写的长篇小说不太一样,与别人的写作方法也不太一样。
这次,我借用了推理小说的壳,写了人物敏感复杂的内心甚至潜意识。人物的对话已经停止,但他们的心理活动却像Wi-Fi那样在相互干扰并默默对话。我毫不犹豫地向人物的内心深处写,在心灵里寻找折射后的现实、加工过的现实、变形的现实,努力寻找何以变形、何以被这样加工、何以被这样折射的原因,相信每个人对现实的加工就是他们的认知、人生态度甚至是他们的哲学。
这样的写作探试让我兴奋,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阅读与写作。那时,我们喜欢阅读有难度的文学作品,喜欢为那些哪怕贡献一点点新意的小说击掌。正因为拥有那样的经历,才有了《回响》对那些文学观念的呼应。(据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