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凸凹
多年前,在读到吴小攀与刘再复的对话录时,我就感到他是一个往深刻里读书的人,不浮光掠影,而是系统地读下去,读遍相关的每个角落,一直把著者逼到角落,无法回答他的追问。他甚至比著者走得还远一些,在意义上追加意义。这好像就是所谓研读,在“别人的热闹里”寂寞,探寻生命感受所能达到的深度、精神领悟所能达到的高度,裨益自己的人生。
给我的感觉,吴小攀很“独立”,在广州这么一个领风气先的地方,他却偏居一隅,读冷书,做冷学问,甘当旁观者,在世俗价值外,寻求终极价值。待读到他的新著《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更印证了我的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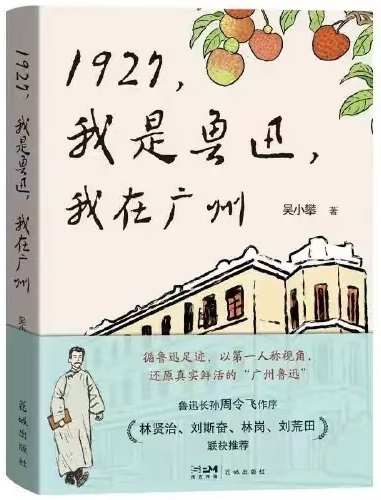
这部书,让我体味到,他是把鲁迅读遍了、读透了,剔沥出鲁迅的生命底色和精神维度,彻底弄清了鲁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很自信地大胆取舍——就选取鲁迅1927年在广州的一段经历瞻望和评析他的一生。
虽然是“一节”生活,但颇可代表鲁迅一生的生命进程。因为广州的这一刻,正是新与旧、传统与反传统、革新(命)与反革新(命)融汇、交织,甚至轮回的历史样相,这与鲁迅的生命状况和精神谱系相暗合。
既知就里,吴小攀便有了文体革命的勇气,他与鲁迅灵魂附体,用鲁迅的感受和语气进行诉说,以避免浅俗和隔膜。就变成了心说,既是鲁迅在说,也是吴小攀在说。
心说属于私语,避免大而无当的大话和空话,要有“隐秘”的语气,要有切真的话题。也就是说,要用语态带出生存的心态,用语调带出生命的格调,让人感受到鲁迅心中的冷与热、寂寞与闹热、绝望与希望、晦暗与光亮。
“鲁迅”的切真话题是什么呢?“言语是一个问题,精神是另一个问题,也许我真的不是这里的人,或者不适合。”“这里”是“这世道”的暗喻,“不适合”是与现世“妥协”而不能的精神困境,因为“我”一入世,就遭冷遇、就遭质疑,只有在“旁观者”的出世状态下,才能感受到些许的“安妥”和“温暖”。换言之,只有在“冷观”和“评说”的状态下,才可以存活,才可以强大。
于是,一旦有了旁观者的“言语”(语气、语态、语调),“同道的稀少”便也堪忍受,矜持和孤傲下,“我”的精神悉数登场,冷眼看“人头涌涌,生活得很”。
所以,刚到广州,热情的青年频频来访,“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情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轻轻地推却了。”“轻轻地推却了”,多么传神地呈现出鲁迅的言语习惯,不禁让人会心一笑。他从来都不妄言,而是看准了再说,以求入木三分;他从来都不贸然地挺身而出,而是打堑壕战,以求得致命一击。
冷眼之下,他果然看清了,广州的夜,其实“寂静得很”,“大钟楼前(虽)经常是万人如海,围巾和旗帜齐飞的革命大操场也退让给这真实的夜……只看到南方的蚊虫在灯下翻飞寻觅的舞姿可耗去许多时间。”于是,他哈哈大笑,嗟叹道:“所谓政府,所谓革命,所谓文学,所谓兄弟,所谓母子,所谓夫妻,是一些多么可笑的东西。这里是化外之地。”因此,“前路似乎触手可及?前路并不触手可及。”
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的“洞彻”,既源自他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深刻把握,对国民性的深切认知,也出自他一贯的“盗天火煮自己的肉”的拿来主义,通过开窗引进西方文明的烛照。因为蒙田也说过类似的一句话,他说,亲朋好友,包括妻子、子女是不重要的,是“自我”的负担。这对向内心深处讨日子过的人来说,其实“自我”也是如黑夜一般的境界,即便心无旁骛,也未必有所得,即不能触手可及。
所以,鲁迅虽身处广州,却是站在“大世界”上进行冷观、思考与言说。因此,他的言语,就是他的心态特征,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就是他的精神内涵。其核心,是处处审视、处处质疑,一切都是深广的所指,一切都是杂文的锋芒——
“大年初三,天气还是那么好,太长久的好不免令人起疑心,甚至担心接下来会有什么相反的东西。”
“广州的学生和青年都把革命游戏化了,正受着过分的娇宠,使人感觉不到真挚和严肃。在广州,有绝叫,有怒吼,但没有思索;有喜悦,有兴奋,但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不会有文学。”
“去的时候不免盼望着,走的时候却是像飞一样地回来。”
但,究竟是在广州,而且是有伊人在侧的广州。鲁迅在享受到日常关怀后,怀疑的底色上,终于有了一抹亮色,心中有了松动的情绪。
他思忖道:“中国人总有活下去的办法,可以儒,可以道,可以释,够用了。一个人,可以无所顾忌到连身体都不顾惜,其实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两个人连结,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更是生命的大道,在转瞬间或假以时日,甚至原谅一切不可原谅。”
这让他有了一点从来没有过的清醒——“我之攻击四万万之社会而得以偷生,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然而,我的话如一箭入海(又何以启蒙)”——“如何能完全超出于人间世呢?—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都没有了。”
于是,他不再一味地出世,开始用人间的视角看广州,“广州似乎一直都是这种淡淡的表情,不卑不亢,与我的脾气倒有几分相宜。”这样一来,他的离开广州,就有了一丝暖意,“在路上的向往,然而也开始莫名地感伤,似乎自己又遗弃了自己的一部分在这里。”这很感人,让人感到,他最终还是跟广州这个伤心之地和解了。
于是,由地理到心里,他不再迟疑,勇敢地恋爱了。“她是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的。”
这越来越短促的言语方式,表达了极其坚定的态度,或可以说,标志着“柔软”的力量堪比刀锋,它(她)能让一个心如坚冰的人冰释隔膜而与生活和解。
如此说来,吴小攀的《1927年,我是鲁迅,我在广州》,就有了广州之外的意义——它或许是第一部关于鲁迅的恋爱本纪,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回忆)还原了当事人的情感现场。它或许是第一部关于鲁迅的心态小说,以贴心贴肺的在场方式,呈现鲁迅的生命流变和心灵脉动。它或许是第一部关于鲁迅的“活”的精神评传,以酷肖的动作、语调、脾气和生活细节,传达出鲁迅之所以是鲁迅的精神消息。
总之,它是一部建立在对鲁迅通透阅读之上的,进入其生命内部,而进行“我说”的文本。它戛然独造,惟妙惟肖地以鲁迅的语气评说鲁迅,以鲁迅的血肉塑造鲁迅的灵魂,一如他本来就活着。
(《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吴小攀著,花城出版社,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