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在线记者 张斌
2025年1月18日下午,川观文学奖(2023年度)颁奖典礼系列活动之一“天府文艺讲坛”名家讲座开启。本届川观文学奖获奖嘉宾、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作家徐剑受邀开讲第一场。
徐剑以《行走的无限与文学的边界》为题,分享了多年来行走与书写的感悟。在他看来,行走不仅是身体的远行,更是心灵的探索。每一次的行走,都是他对自我、对世界的重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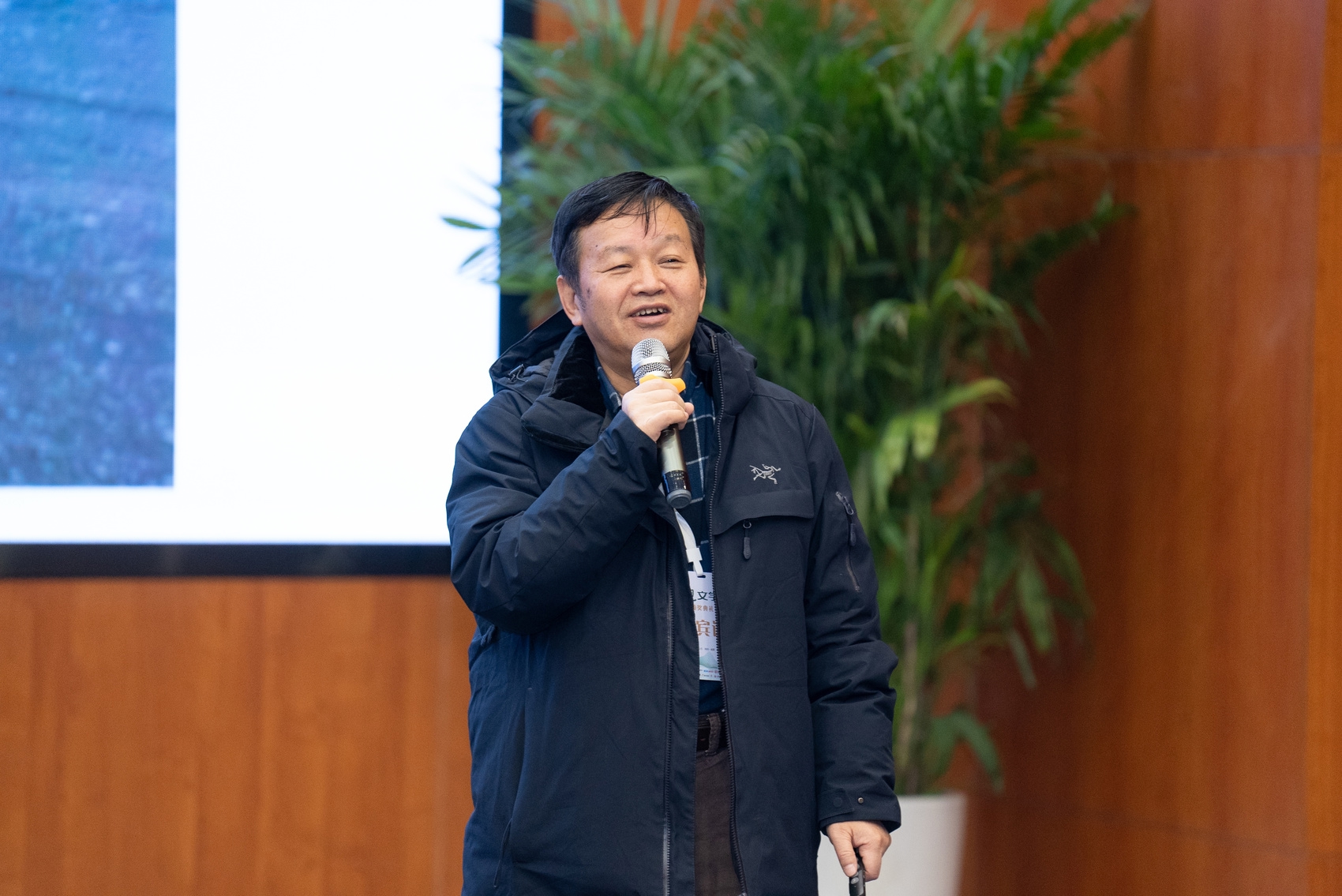
徐剑在“天府文艺讲坛”开讲。李强 摄
本期《川观书评》特将此演讲稿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在行走中寻找精神原乡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拥有两个原乡:一个是童年的原乡,另一个则是行走的疆域。无论哪个原乡,都能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滋养。
一个作家,不管是天才型的还是生活型的,要不守住自己的家乡写,要不守住自己的远方写。关于行走、远方,贯穿了我的半生。
我出生在云南昆明,16岁时投身军旅,这一走就是44年零1个月。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我写下了近800万字的作品,包括《大国长剑》《东方哈达》《大国重器》《经幡》《天晓1921》《西藏妈妈》等。
多年来,我给自己立下了“三不写”的规矩:自己走不到的地方不写,自己没有听说过的故事不写,自己没有看到的地方不写。正是这种对真实与行走的执着追求,让我在无数次濒临极限的行走中,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了生命的力量与希望。
受老首长阴法唐先生等人的影响,我将行走的足迹放在青藏高原。我曾24次前往那里,最近的一次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从昆仑山东部走到西部,跨越青海和新疆。为了创作《昆仑山传》,我深入古道、深入村庄、深入荒原,探寻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与细节。
在前往长江源头的格拉丹东,我和友人在雪地中发现了雪豹的足迹。那清晰的脚印,如同朵朵莲花。雪豹在那天可能没有吃的了,就跑到村庄里偷羊。天亮了,看羊人开始出来了,它就向雪山上跑了。此情此景,让我将天上的雪豹和人间的烟火联想在了一起。
在青海的约古宗列曲,我亲眼目睹了黄河源头那小小的池塘。虽然它与我想象中的黄河源头相差甚远,但它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坚韧。“黄河不拒涓流,最终汇聚成浩浩荡荡的大河。”这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
在沱沱河上的雁翅坪,我联想到这个地名的由来:慕生忠老将军当年在修青藏公路时,看到天上的灰头雁飞过,掉了几根羽毛下来,他就起了一个很美的名字:雁翅坪。这属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独有的浪漫主义情怀。
行走的路上有看不尽的美景,关于行走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此。行走青藏高原,让我拥有一种观天下、看中国、看4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变化的视角。

徐剑在克里雅古道采风。(徐剑供图)
在行走中感悟生命意义
我常常问自己:人生为什么要行走?经过这么多年的行走与书写,我似乎有了答案:行走看天下,会带给你一种无尽的感受,会让你与历史、与古人有一种灵魂上的勾连。
在柴达木盆地的茫崖市,我曾随科考队员深入这里的“大地之眼”景观。一片云过来后,我联想到,大唐帝国的遣吐蕃使刘元鼎走过昆仑山的星宿海,那里有无数双“大地之眼”,还有大唐出使古天竺的王玄策也经过那里,这些历史人物早已不在。此刻,一批科考队员深入这里,我有一种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的感觉。瞬间,无尽的沧桑感涌上心头。
在新疆的克里雅古道,我看到了草色连天的草场、牧场,令我慨叹自然的神奇美好。在几十年前,我们有一支队伍(进藏先遣连)从新疆翻山越岭去解放西藏。这条路长达600多公里,开车都得两三天,当初他们骑马翻山,艰难可想而知。
每一次行走,也是一次与大地、与神灵的对话,都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深刻领悟。在怒江第一湾的丙中洛,我看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景;在鄂陵湖边、在阿尔金山,我看到成群的藏野驴、魂牵梦绕的野牦牛,生命的野性令我震撼,久久难以忘怀;在长江源头的石头上,点地梅长得很小却很美,那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在青海囊谦县的一个废弃村庄,空地上长满野生的黑枸杞,顽强且坚韧。
行走在青藏高原,我见证了无数的生命奇迹,也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1990年,我第一次踏上高原,从格尔木出发到了西藏日喀则,却因高反昏迷了3天。
然而,这并没有阻挡我对青藏高原的热爱与执着。此后,我多次前往西藏,见证那里的风土人情与自然生态。作为一名作家,我深知行走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中,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在创作中感悟行走的无限
此前行走的生死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因此,我在一次次采访中,不断超越自我,追求极致。

徐剑在采访途中。(徐剑供图)
《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这本书的采访写作,就充满了不断克服艰难险阻的历程。
进藏采访前,受客观因素影响,日程一再迁延。好不容易等到我62岁生日的第二天启程,却一再遇到突发情况。在成都双流机场候机等待飞往西藏昌都的途中,被告知邦达机场突降大雪航班延误。我从早晨6点到等到正午12点,延误,再延误,最终飞往昌都的航班取消。坐在候机室里,我再也按捺不住进藏采访的愿望,决定不再等待,绕道飞往玉树,乘坐汽车前往昌都市贡觉县。
在青藏高原上采访行走,最好少讲话,因为说话越多高原反应就越强烈。可是,我想要了解到农牧民群众更多的喜怒哀乐,就得和他们讲话,这是一个作家必备的工作技能与职责。在写作《金青稞》时,我用了52天跑完19个贫困县,每天坐车行走近400公里,不断地和农牧民群众攀谈采访。在如此情境下,能找到包里剩下的最后一个苹果或得到一罐氧气,我都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
在行走中,我看到青藏高原的壮美与神奇,也看到那里人民的坚韧与善良。在采访写作《西藏妈妈》时,我从昌都市第一儿童福利院开始,经过横断山脉,横穿万里羌塘,在那曲市儿童福利院采访3天;再抵达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的双湖县,重点采访“双集中”试点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此后,一路西行前往阿里,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而行,抵达日喀则,再到拉萨、山南、林芝,一路走了7家地市级儿童福利院,共采访了100多位“妈妈”。
那些阿妈拉、未生娘(未婚女子)不分年龄与民族,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藏妈妈”,或者说“爱心妈妈”。她们将自己与福利院的孩子们紧紧连结在一起,以温暖大爱抚育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她们的情感,如同一条情感的雅鲁藏布江。江有多深,她们的情感就有多深,爱就有多深。
在写作中,我将上述经历与感受融入我的作品中,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青藏高原,了解那里的人民与文化。而关于我的行走,还在继续,我也期待以真实的故事、真挚的情感书写时代,留下这个时代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