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江
邓经武教授的《巴蜀文化通史·文学卷》,撰写10多年,篇幅60万字,是四川“重大文化建设工程”项目内容之一。该工程由川渝两地学术界某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进行多卷本《巴蜀文化通史》撰写的。
《巴蜀文化通史》主编之一章玉钧指出:《巴蜀文化通史》是“巴蜀文化”概念提出80多年来“首次大的学术集成”,“成为首部纵横贯通、覆盖面广、体量超大的巴蜀文化史,在全国已出的各种区域文化通史中,当属编撰体例新、时间跨度长、内容浩繁的一部。”
邓经武先是受聘为该项工程的编委,继后接手其中《文学卷》的全部撰写工作。邓经武在该研究领域除发表数十篇专题研究论文外,还先后出版专著《20世纪巴蜀文学》《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等。《巴蜀文化通史·文学卷》材料更丰富,体系更完整,论述逻辑更严密。对某些文学现象的表述更为清晰,如关于元代文学的巴蜀“流寓文学”和江南地区“蜀二代”作家群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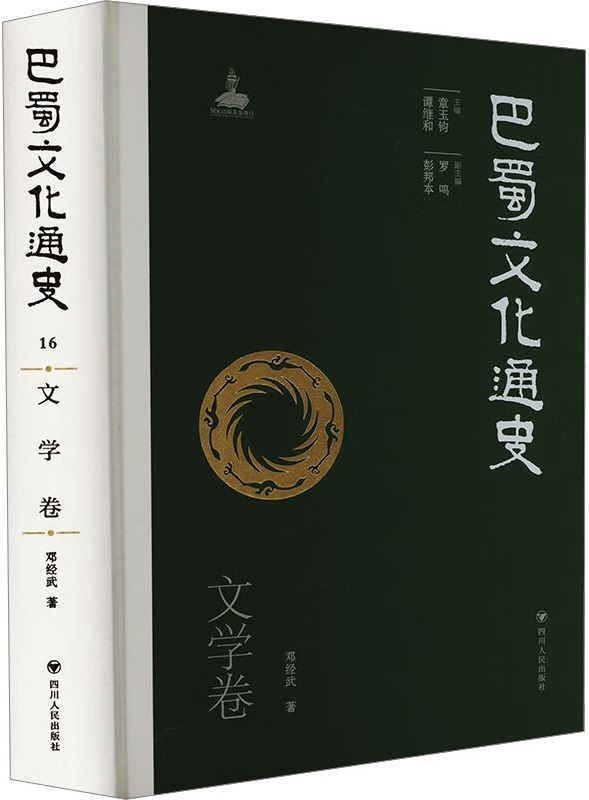
《巴蜀文化通史·文学卷》紧扣地域文化主线,串联起“蜀人”所记之“蜀事”,所叙之“蜀情”,所体之“蜀风”,将巴蜀文学和巴蜀社会历史文化紧密联系,揭示了5000年来巴蜀文学生成与传递、文学理论发展,以及文化运行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分展现了巴蜀文学审人、审美、审自由的地域个性。如李白“谑浪万古贤,以为儿童剧”,蔑视权威,逍遥放任;苏洵自矜狂放,傲睨天下;杨慎在明朝大兴党狱的背景下,高举“性情”大旗……他们身上的狂悖、自我,乃至江湖气,都是巴蜀大地刻下的文化印记。
从大地与人的互动关系中,思考本土文化建设,追求巴蜀大地的精魂所在;以人类文化学的眼光,用文艺美学视角,着眼于四川—巴蜀大盆地自生命发生以来,直至当下的社会整个运行过程——这既是该书的基本学术路径,也是最大的学术特色。
在该书中可以看到:从骚体赋到汉大赋,司马相如为汉赋的发展奠定地基,成为“大汉时代的显赫声威的代言人”;严君平、扬雄师徒的道家“玄学”,成为魏晋社会思潮的主流;陈子昂用健康的审美标准,催发了唐诗的蓬勃;从华而不实到文以载道,田锡、苏轼跳出古文之统,提出了全新的阐释;“明代著述第一”的杨慎,几乎做出了“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创造;在宗唐还是宗宋的争论中,清代张问陶独抒性灵,大胆挥洒真情。而在现代文学中,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等人,在文学大变革中,表现出反叛一切旧式美学、冲破一切封建规范的精神,从而获得全国影响。
口语化的语言、不拘音律的表达、出世的心态、恣意的情感等精神图谱,都成为巴蜀文学中随处可循的标志。巴蜀作家不被形式所控制,不被传统所引导,自带的对美的不懈追求,驱使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一亩方田。
作者认为,巴蜀文学都有“鲜明的自我意识表现和坦率真诚吟咏生命体验”的特点,也可称为某种意义上的情感自由。书中论述了司马相如“非常之人”的骄狂,扬雄的“壮夫”志向等。凡是受格律限制无法自由挥洒的言语,均被大胆突破,正如李白诗中时常三言、五言、七言掺杂,长短不一,灵动自然;何其芳诗句整饬,只用连锁的意象,营造忧郁的氛围,婉转传情。纯粹的抒情,如书中引述的清代张问陶的“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所论。
书中不乏值得注意的论述和观点。
在论述巴蜀上古神话时,从童年人类的图腾崇拜,说到巴蜀先民的蛇图腾,又引证《说文解字》以及闻一多的研究成果,从文字文化学的角度指出:“蚩、禹、蚕、蜀、巴等文字,都与蛇形长‘虫’有关。”将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华胥、伏羲、女娲、夏禹,还有蛇图腾与大石崇拜、杜宇化鸟、廪君化虎、鱼盐女神、巫峡神女等,都置放于中国文化开端的整体格局中。
同时展开文明互鉴的横向比较,如“童年时期的人类,不管是因为偷吃‘智慧之果’的意识萌生,还是在‘混沌初开’中睁开眼睛”等阐释。又把这些神话传说与北方中原进行比较,说明大盆地“客观世界的形态表象、天地万物的循环往复方式等,都被投射于其思维和思想中,使之一切生存创造活动都带着客观存在的独特印记”。
对沉寂期的魏晋巴蜀文学,该书用左思《蜀都赋》、王羲之的《成都帖》、王粲对巴渝舞曲的改编、常景咏吟巴蜀前贤的组诗,还有郭璞的《巫咸山赋》和《盐池赋》,尤其是《江赋》等巴蜀题材,以及张载的剑阁铭和郦道元的《三峡》等,专节展示“魏晋文学的巴蜀情结”,至少从体例构架上是一个创见。
还有,涉及屈原时,该书提出了一个大胆新见:“屈原的艺术成就,离不开巴蜀文学的影响。因为,如果屈原故里确在秭归,他就应该是巴人,秭归属巴地;他长时期生活于郢都,而郢都盛行流传着‘下里巴人’歌舞,成百上千个人同声传唱的‘巴人歌’,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他后来被流放于巴人聚居甚众的湘沅流域,其搜集的民间歌词中肯定有不少的巴人歌词。他的作品中充盈着大量的巴地景物、地名和人物及传说故事,如‘巫山’、‘高唐’、‘王乔’‘彭祖’等,其《天问》中关于‘灵蛇吞象,厥大何如’的思考,正是‘巴蛇吞象’神话原型和巴地民间文学的直接摹本”。
如此种种创新性洞见,都显示出该书的学术深度与宏大的审美视野。
在邓经武的书写中,巴蜀大地与叛逆、创造、独立、生动、华丽、狂放这些别具一格的视觉图像,产生了深度联系,凸显出完全不同的地域品格。在此,笔者想用一个词予以概括——自由。
这种自由,让巴蜀人民不以世俗为准绳,遵从本心,说自己想说的,做自己想做的;这种自由,让巴蜀文学有引领革新的勇气,立自己的论,树个人之风;这种自由,也让巴蜀文化中满含着真情实感,风雅兴寄,抒自己的情,寄自己的志。
这一切,根系都在这样的论述中:“域内相当于两个法国的辽阔面积,为一种文化的发生、繁衍、运行、壮大提供了适当的空间;境内水系纵横交错,平原、浅丘、高山、岭谷等多种地形地貌及各种地表裸露色彩兼备,以及因为亚热带气候的温湿宜人所带来的四季变化分明、自然景观缤纷多姿,都直接陶冶熏染着巴蜀人对‘美’的敏感心理机制。‘喜艳秾’‘好华美’‘重色彩’以及味觉的‘好辛香’‘美滋味’等地域文化美学的形成,就正是被这种‘存在’的客观前提所决定的。”
同时引证秦代贡品西蜀丹青、汉代黄润细密的蜀布、唐代光鲜亮丽的蜀锦和邛三彩,明清的绵竹年画等,乃至广汉三星堆以及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精美纹饰和艳丽着色等具象形态的艺术进行互证。
通过通史式的地域文化书写,巴蜀文脉以极强的连续性和突出的统一性,展现在众人面前。该书按时间顺序进行论述,从远古时期“巴”“蜀”二字的象形之意写起,结束于对巴蜀新生代诗群的梳理。
书中所引扬雄将“蜀”解为“獨”,是强调“不与外方同”等,具有特殊的表现力。巴蜀大地上的自由风气,赋予这种独特以底气。司马相如、李白们的大胆挥洒,与新时期诗人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首尾映衬;其间,又将各时期文人从文化传统中自由发扬的新风相互勾连,逐一评说:如扬雄对蜀地之物产文化细致描写的《蜀都赋》、李劼人、沙汀笔下泼辣重义的江湖题材……得出的结论是:“巴蜀地区远离中原,长期处于中央政权和主流统治文化的‘边缘’状态,长时期被轻视为‘西僻之国’;却又因物产丰足、疆域辽阔和人口众多,而常居‘戎狄之长’地位。其间还常因‘蜀山兀,阿房出’的巨大财力、‘扬一益二’的经济优势和‘比之齐鲁’的文化繁荣状况,而倍增骄狂之态。”
又如说苏轼的“巴蜀文化意识的自觉”,认为这种自觉代表着苏轼对巴蜀地域文化的认同,也是一个地域群体的地域意识觉醒。即苏轼“以道家的自由通达看待人生,以蜀禅‘自心是佛’保持着心灵的宁静,并带有巴蜀人文特有的诙谐机趣去面对一切神圣和权威”。
总而言之,本书紧扣巴蜀地域文学的脉络,抒写巴蜀大地的生命记忆,展现巴蜀文化的迷人风采。这让本应作为史学研究的著述,也从某个程度上沾染上“自由”的风气,体现出不同于其他文学史写作之“新”。
一是新在研究方法。
作者梳理了数千年来巴蜀文学的经典要目,以文学通史突出地域文化精神,如李白对前辈乡贤司马相如等的迷恋和创作模仿、陈子昂理论与创作中的巴蜀文化美学浓艳华美特征的呈现,郭沫若“吾乡苏长公”的骄傲等。同时,从地域文化意识出发,强调巴蜀文化与巴蜀文学的一体性;灵活运用流变研究、比较研究和文本细读,让巴蜀精神在笔下绽放。
二是新在研究视角。
“两种有异质的文化的碰撞和差异对比,使他能够用清醒的主体意识去观照、选择和认同化取,以确立自己的创造个性和建构自己作品的文化品格。”这是作者评价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李劼人,而这也正是作者在新时代研究所存在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二元对立中,寻找到的解决之道——地域文化研究。
作者巧妙地将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都融化到巴蜀文学的框架中。如突出和强调何其芳《画梦录》的艺术辉煌,原因在于其对晚唐西蜀《花间词》的化取,以及对西方现代派技巧的吸收等。总结出巴蜀文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和相同特征,体现出鲜明的全局性视野,也让巴蜀文化焕发新生。
三是新在方法论自觉。
本书真正做到文学、文化不分家,从文化的革新写文学变迁,如先写盛唐气象,再写巴蜀狂歌诗史;先写政治、文化革命,再写巴蜀怪杰魏明伦的戏剧创新探索。本书立足巴蜀文学作品研究,却在行文中不断流露巴蜀文化之意蕴,让“骄狂执着”“浓郁鲜明”“张扬个性”“形式自由”“大胆冲决”“对抗世俗”等巴蜀文化精神,走进每个读者的心中。
(《巴蜀文化通史·文学卷》,邓经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
作者简介
罗江,成都大学文新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