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的演变过程,折射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研究汉语其实是在研究中国文化背后的底层逻辑
·文化交涉有两个超越,一个是超越国家民族性的研究框架,另一个是超越以往人文科学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框架。这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
·语言学研究不能只从语言内部研究语言本身,我们应该从外部世界寻找参照物,以外围视角来补充现有研究
·“从文化周边看中心”是强调文化内外参照,它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更全面和深入,更好地理解文化整体在互动中的生成

人
物
简
介
内田庆市,日本著名汉学家,“文化交涉学”创建者。曾任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关西大学图书馆馆长等。现为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副会长、东亚文化交涉学会常务副会长、日本中国语检定协会理事长等。曾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厦门大学执教。
主要从事近代东西语言文化交涉史研究,主要著述有《京华杂拾-北京官话资料8种》《造洋饭书的研究》《华英通语-解题与影印》《拜客训示的研究》《官话指南的书志研究》《字典集成-影印与解题》《汉译伊索集》《文化交涉学与语言接触-汉语语言学的周边方法论》《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的研究》等30余种。
四川在线记者 王国平 摄影 李强
汉语,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符码。数千年的时间里,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汉语也得到了极大丰富。同时,汉语又以其独特的文化性影响着世界,并不断吸引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研究。
日本著名汉学家内田庆市,从事汉语教学、研究40余年。在以东西方语言接触史为基础做汉语语法研究的过程中,奠基并创建了“文化交涉学”。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关注表面上的语言接触,更注重语言接触背后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多重异质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如此可以更好把握汉语研究的整体性、多样性与动态性。
近日,在完成对北京、山东等地高校的访问、讲学后,内田庆市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的采访。内田庆市说,汉语的演变过程,折射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研究汉语其实是在研究中国文化背后的底层逻辑。

内田庆市
喜欢鲁迅的汉语研究者
内田庆市很早就对语言学产生浓厚兴趣。读高中时,他从书店买回《源氏物语》《枕草子》《徒然草》等日本古典名著,拆解分析其中的词,并接触到一些语法理论。与此同时,结合《史记》《十八史略》《古文真宝》等白话版本,他也学习了一些汉文知识。
1969年,内田庆市考入大学。因为希望毕业后能成为一名小学老师,他最初选择的专业是教育系的国文科。“按照规定,国文科的课程中必须选修第二外语汉语,所以大学一年级时慢慢对汉语产生了兴趣。”
鲁迅是内田庆市最早接触到的中国作家之一,至今仍然热爱。喜欢鲁迅有两个原因:一是鲁迅的文字本身所具有的穿透力和批判性,让他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种力量;二是鲁迅曾在日本留学,特别是鲁迅文章中的“藤野先生”——藤野严九郎,和内田庆市是日本福井县的老乡。“这让我感觉很亲切,也越发喜欢鲁迅。那时我们几个人组织了一个‘鲁迅读书会’,常常聚在一起,交流阅读和学习心得。”内田庆市说。
到大学三年级时,内田庆市想成为一名汉语研究者,决定转变专业方向,在大学毕业后到大阪市立大学的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学习研究汉语。
在大学院里,内田庆市师从香坂顺一、宫田一郎等日本汉语学界的著名学者。此后,他又攻读博士学位,继续研究近代汉语的语法和词汇。1978年,在完成博士课程后,回到家乡的福井大学执教。
1981年,内田庆市与当时研究英语语法的日本学者宫下真二教授合编了《现代语言学批判》一书。他的论文《〈马氏文通〉(1898)以前中国人的词语分类》被收录书中,这是他早期探讨汉语语法问题比较重要的一篇论文。
《马氏文通》是清末学者、外交家马建忠创作的语言学著作,于1898年首次出版。学界评价称,该书把西方的语法学成功地引进中国,创立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词类问题是语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在《马氏文通》刊行前,中国的词类研究主要是对实词和虚词进行诠释和说明。
在论文中,内田庆市阐述了中国传统的“虚实论”,他认为这一理论与日本学者的词辞论,以及17世纪中期在法国产生的普遍唯理语法学派的词类二分法惊人的一致,即文章是由主体表达和客体表达组合而成的,并指出这是语言所具备的普遍性,他引用《马氏文通》中的“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来证明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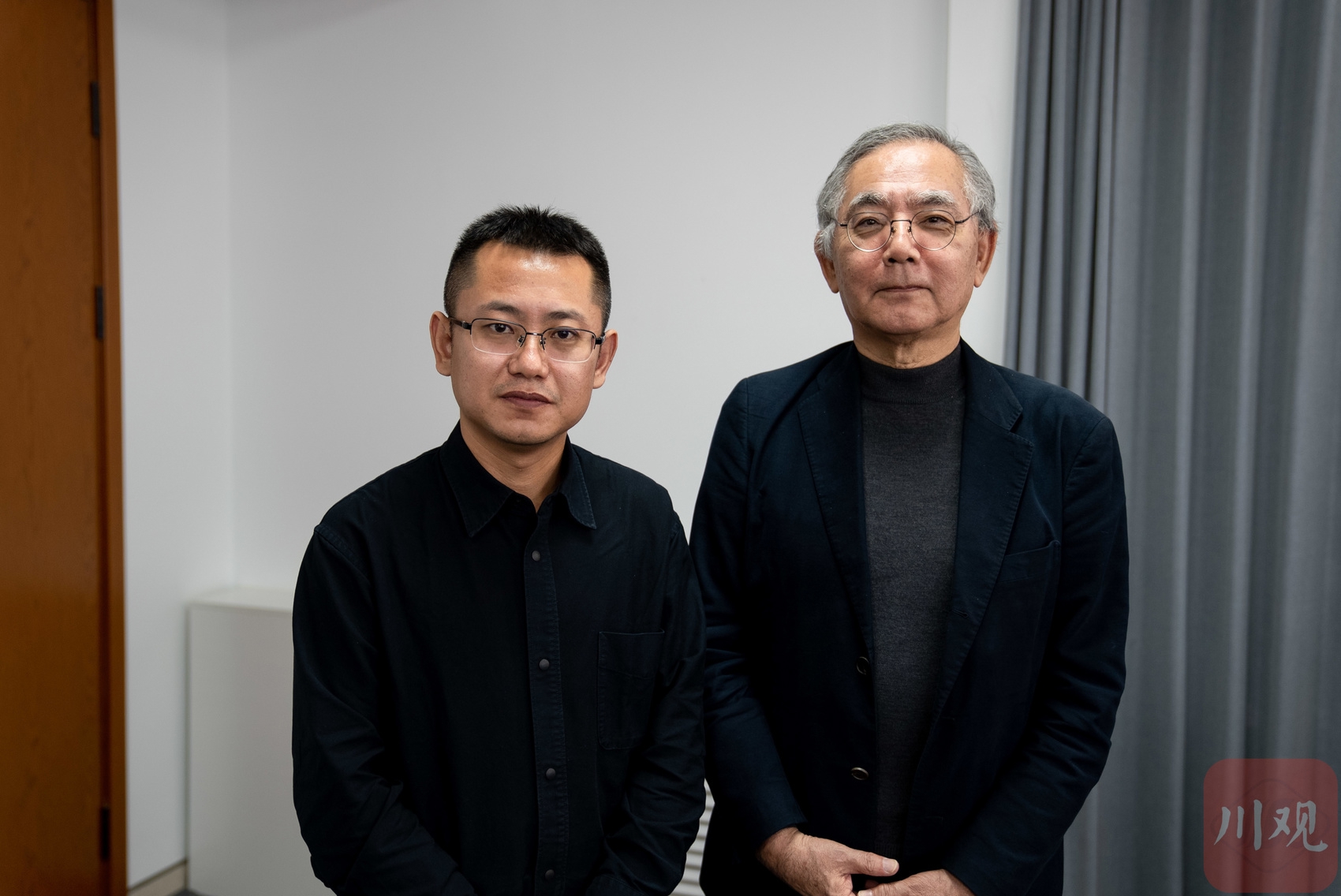
四川在线记者和内田庆市
上海之行改变其研究方向
在内田庆市的学术之路上,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一次上海之行。1987年到1988年,内田庆市在上海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跟随语言学家许宝华教授进行汉语研究,具体方向为上海方言。学习之余,内田庆市最大的乐趣是买书。“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坐55路公交车去上海福州路的一家旧书店,虽然并不是每天都有新书上架,但因为担心偶尔上架的一些好书被人买走了,所以每天都去看看。”内田庆市说,后来回日本时,图书装了50多个箱子。
有一次,内田庆市在书店里看到一捆已经包好的书,店员说是已经被人买走了的。询问之后得知,买书者是周振鹤先生。周振鹤当时是复旦大学的一名青年学者,内田庆市虽然不认识他,但读过周振鹤和游汝杰先生合作撰写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对于这本书他印象深刻。后来在书店里,内田庆市结识了周振鹤。
“认识之后,他经常到我的住处来问我,都买到了什么好书。”内田庆市回忆说,两人对于近代文献的收藏,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两人的友谊保持至今。
周振鹤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并旁及文化语言学、中外语言接触史等方面。正是这次相遇,触动了内田庆市对于语言研究方法的思考。
当时,复旦一群青年学者还组织了一个“现代语言学”沙龙,除了语言专业的学者外,不少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参与其中。内田庆市偶然参加后觉得很有意思,便加入交流。“沙龙里有个口号,叫‘吾爱吾师,更爱真理’,参加讨论的学者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内田庆市说,这些复旦学者的研究也很有特点,将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这样就比仅仅做词汇研究更深入,“这一研究思路我很赞同,我认为单纯就语言研究语言是无法深入的。”
通过与复旦学者的深度交流,内田庆市深受启发。回到日本以后,他便决定改变研究方向,由原本单纯的语言词汇研究转向文化交涉和语言接触领域。这对于他来说,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因为当时日本还没有人从文化角度来研究汉语。“日本学者还是继续用原来的方法研究汉语,主要还是对汉语的白话材料进行研究。”内田庆市说,后来他在和西方学者的交流中,使自己的研究逐渐聚焦,研究方法也开始清晰,即结合“西学东渐”的过程,展开对近代汉语的历史语言学研究。

内田庆市在学术会议上
奠基并创建“文化交涉学”
结束复旦大学访问研究返回日本后,内田庆市在关西大学文学部任教,开始不断丰富“文化交涉学”的内涵,并积极开展学科建设。内田庆市说,语言接触是文化交涉的前提,文化差异的最主要表征亦在于语言。
2007年,在内田庆市的推动下,关西大学成功申请到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全球卓越研究中心教育研究基金项目,主题为“东亚文化交涉学教学研究基地的形成”。该基金项目代表了日本人文科学研究最高水平。
在有关文化交涉学的定义中,内田庆市写道:“文化交涉学突破以往以国家或民族为分析单位的局限,设定了东亚这样一个具有某种综合性质的文化综合体,关注其内部所存在的主要是某个领域的文物、制度等的专门研究,从综合性的立场出发,以多元化视角对文化交涉的整体形态进行阐释。”
此后,内田庆市带领团队于2008年在东亚文化交涉学教学研究基地内建立了东亚文化研究科,开设了东亚文化交涉学专业。至此,在不断深化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后,由内田庆市奠基并开创的“文化交涉学”,成功创建为日本的一级学科。关西大学也因其独具特色的学术研究,成为东亚文化研究领域的一座重镇。
近年来,“文化交涉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问体系,以东亚区域为统合整体,着眼于其域内文化产生、传播、接触、变容的多元化行为,为语言接触、文化交流、知识翻译等研究提供复合、综合、多维的分析视角,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
2014年底,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内田庆市作为关西大学的代表专程到北京参加活动。内田庆市告诉他在北外的好友:“全球史的专门史研究,也是我梦寐以求的方向。”因为,文化交涉有两个超越,一个是超越国家民族性的研究框架,另一个是超越以往人文科学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框架。比如在东亚范围内,需要以多角度和综合性的观点来解析文化交涉的形态,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2017年,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9届国际学术大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翌年11月,该校成立“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中心”,特邀内田庆市担任中心主任。2021年,内田庆市从关西大学退休。在他的执教生涯里,培养了众多学生,既有日本本土的,也有来自欧美的,还有50余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如今他们在北京、山东、四川等省市的高校继续从事相关研究。
对
话
通过“他者”视角更好认识汉语
关注东亚内部所发生的有关文化现象
记者:什么是文化交涉学?
内田庆市:以往的文化交流研究,主要积累的是针对个别专门领域的文物及制度所进行的事例研究。虽然语言思想、民族、宗教、文学、历史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个别叙述并积累了一定的成就,但在文化交涉的整体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方面仍然有很多未被开发的领域,这也恰恰反映出现代人文科学研究的现状,就是不同学科虽然都把同一事物作为研究对象,却缺乏跨学科的接触或联系,因而失去了研究的整体性,也难以把握文化接触和变异的多样性与动态性。
另外,以往的文化交流研究的前提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框架。比如,日中交流史的研究现状,大多受到了日本和中国国家框架的束缚。17—19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在中国被称为“清朝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日本则被称为“江户·明治时期的日中文化交流”,从而忽视了东亚多元的文化交流对中日交流的影响。
我们所提倡的文化交涉学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它突破了以往以国家或民族为分析单位而设定东亚这样一个具有某种统合性质的文化综合体,关注其内部所发生的有关文化的形成、传播、接触以及变迁现象,从综合性的立场出发以多元化的视角对文化交涉的整体形态进行阐释。
记者:在人文研究领域,一般用“交流”较多,比如“跨文化交流”“跨学科交流”等,您为什么用“交涉”一词?
内田庆市:这是我被问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第650页)对“交流”的解释是“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给对方”,如物资交流、文化交流、交流工作经验等。而对“交涉”的解释是“跟对方商量解决有关的问题”,英语里有个类似的词,就是negotiation。根据《汉语大词典》第二卷第335页中的记载,“交流”有“犹言来往”“谓相互传播;交换”的意思;而“交涉”既包含“接触;往来”,即英语中的interaction,也包含“跟对方协商以期解决问题”的意思。因此,我们认为“交涉”包含“交流”且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加契合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范围和目标。
“中国”是文化交涉学的重要关键词
记者:文化交涉学中有哪些关键词?
内田庆市:根据文化交涉学的研究主题和范围,我们设定这样一些关键词,比如“跨领域,跨文化”“跨地域”“多对多”“多元化的视角”“从文化周边看中心”等。其中,“从文化周边看中心”是文化交涉学的方法论。从地理上看,语言学研究不能只从语言内部研究语言本身,我们应该从外部世界寻找参照物,以外围视角来补充现有研究。比如说,中国的汉语语言学家在研究汉语的时候,使用的参考资料主要是中国人编写的。实际上周边的资料也很重要,比方说欧美传教士编的各种汉语课本,这是以外国人的视角看汉语。关注这些资料就是从内部跳出来,从外部去观察内部。
从研究领域看,需要拥有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即语言研究学者要看看历史研究学者的看法、历史研究学者听听社会研究学者的看法。这是用外围的研究视角,去补充我们的既有研究。这样的研究视野对一个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举两个例子,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是1898年问世的《马氏文通》。而西方早在16世纪就开始研究汉语,用自己的理论系统来阐释汉语的具体特点、总结汉语的语法现象。另外,一些在中国人看来理所当然的汉语现象,在西方人看来都是值得研究的方向。比如量词的使用。英语里基本只用“a”来表述,但是中国人会说一本书、一把椅子、一张桌子等,他们觉得很特别,于是开始研究汉语里的量词用法。
所以,“从文化周边看中心”是强调文化内外参照,它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更全面和深入,更好地理解文化整体在互动中的生成。要注意的是,我们提倡的“从文化周边看中心”这一观点中,中心与周边并不是固定的,它们可以相互转换。研究中国的问题时,日本和韩国就是边缘,研究日本的问题时,中国和韩国就是边缘。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是文化交涉学中的重要关键词。
记者:文化交涉学的研究方法,对认识中国文化有何意义?
内田庆市:传统的亚洲文化研究试图在一国框架内把握日本文化、中国文化等的特质及其形成,而关注“中心”或“核心”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将非中心的“周边”剥离开来,仅分析“中心”或“核心”,以提取纯化的文化现象。
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不同文化的接触是持续发生的,且这些文化接触现象恰恰更多地发生在被剥离的“周边”。所以,只有挖掘“周边”,才能把握文化交涉的活力。在这种活力的推动下,A文化被显露在B文化民众的视线之下,并通过碰撞、转换和融合被B文化民众接受和确立。文化交涉学,就是通过“他者”视角重新诠释的文化形象揭示构成文化本质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在传统的以中心为导向的文化研究中是看不到的。我们称这种关注丰富“周边”的视角为“周边方法”,并认为它是形成文化交涉学的基本方法论。
汉字在东亚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从文化交涉学看,汉语或汉字对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起到了什么作用?
内田庆市:历史上,在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主要包括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这些国家和地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曾以汉字作为官方文字,以儒家文化为思想伦理基础,在接收汉文化的同时,又融合发展出自身民族语言和文化,汉字在东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即使是在当下的日本和韩国,民众仍将儒家文化作为重要的个人修养和社会伦理规范。我自己就有一本《论语》日历,每天可以读到《论语》中的一个名句。我的哲学老师3岁时开始学习《三字经》《十三经》,日本有的公立小学甚至要求学生每天诵读《论语》。
记者:在这些文化交流中,汉语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内田庆市:数十年来,我一直专注于汉语从古至今的演变。文化交流对汉语的影响,不仅是发生在东亚,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是全球史的一部分。中西语言文化的接触和互动,给双方带来重要影响。非常典型的,有三个时期:
首先是从西汉时期开始,随着丝绸之路的打通,从西域来的“物”,丰富了汉语。比如“葡萄”,是“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而还,中国始有”,古汉语里有葡和萄这两个字,但之前没有“葡萄”这个词,这个词其实是源于古波斯语到大宛语,再经过中文音译,最后有了意义。又比如“狮子”,《汉书》里写为“师子”,还有“玻璃”“琵琶”,等等,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使汉语中产生了新的词语。
再看唐朝时期,随着佛教从印度东传,很多佛教词语融入汉语,比如说“世界”“现在”“圆满”“因果”等,这些词语还在汉语中形成了一定文化内容,并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最近一次大规模文化接触,始发于16世纪末的“西学东渐”过程。明末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西方的宗教、科学、文化等也一并输入。从此以后,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都被卷入了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中。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流往来频繁,不仅对中国,也对日本的文字、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期间汉语里出现了很多“译词”,包含丰富的新概念。比如,汉语里本没有“科学”(science)一词,直到晚清,知识分子才了解到这一西方概念,但并未直接使用它。后来日本率先将“science”翻译成“科学”,梁启超等人将这个词带回中国。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在文化交流中,汉语得到了极大丰富,也揭示了汉语及其背后文化的演变路径。特别是自19世纪以后,大量类似的新概念进入到汉语中,对应产生了大量新词语,助推了汉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反过来也一样。我举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洋泾浜英语。“好久不见”的英文是“Long time no see”,这是对汉语语言的直译,并不符合英语表述规范。近代上海开埠后,中外贸易往来密切,当时中国的商人并不懂英语语法,很多对话是按照汉语逻辑直接转化为英语表达,但是并不影响双方的理解,并就此沿用了下来。
这样有趣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意大利人经常在喝酒干杯或是表达客气的时候,会说“Chin Chin”,其实就是从汉语的“请、请”来的。他们读不出“qing”中的“q”这个音,所以就成了“Chin”。
只有了解对方的文化才能交流
记者:在文化交流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就是“翻译”。
内田庆市:对的。不同文化的接触或交流,一般通过语言来进行。这时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翻译。
翻译一般可以认为是用某种语言的词汇代替另一种语言的词汇,但实际上翻译并不是那么简单。语言的背景应该有人的存在和语境。某种语言里的词汇是使用那个语言的民族的“认识”的集合。换句话说,语言就是人认识的表现,是民族历史、思维方式、文化的反映。如此说来语言就是文化。站在这样的语言观的立场上,我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词汇的代替,也是文化的问题或者接受文化的态度和方法的问题。
所以“翻译”的等价是什么?不是看得见的“形式”,而是看不见的“价值”,这个价值是把某个民族的思维、文化集合或抽象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龟兔赛跑”这个故事,出自1840年的《意拾喻言》,也就是《伊索寓言》。
《意拾喻言》的翻译者是当时英国驻华外交官罗伯聃,在他翻译的这本书里还出现了“盘古初”“山海经载”“神农时”“虞舜间”“齐人有一妻妾”等。甚至西方神话中的人物也成了中国人熟知的人物,比如把“Diana(月神狄安娜)”翻成“嫦娥”,把“Jupiter(天神朱庇特)”翻成“北帝”等。这样罗伯聃的伊索穿着“中国人的衣服”上台了,完全被中国同化了,跟后来中国译书大家林纾翻译的《伊索寓言》(1903年出版)有很大不同。
我认为,翻译最重要的是要对对方的语言、文明秉持一种“谦虚”和尊重的态度,只有了解对方的文化才能交流。
无论如何,以外文资料为主的周边资料对于汉语各领域的研究确实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这会使汉语各领域的研究更加快速地发展起来。文化交涉学就是一门通过这样的视角来研究语言习惯的学科,学习语言要先建立在学习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但“文化”的概念也很广泛,比如历史观、美学观和思维方式,都包含其中。
记者:如今在日本学习汉语的人多吗?
内田庆市:我的导师香坂顺一是日本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权威,推动了日本“中国语检定考试”,对日本的汉语教育有卓越贡献。继承先师遗志,我也一直致力于汉语的推广,现在日本国内汉语水平考试是由我主持的。日本有600多所高中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授,而每年参加这个考试的人数大概是3万人,其中在我任教的关西大学的汉语学习者就相当多,现在有6000多人学习汉语。我住在大阪,基本上每个月要去东京3次,为“中国语检定考试”开展一些有关标准制定、考试内容以及结果评定等工作。
在不断研究中,我愈发能体会汉语的独特魅力。希望在日本乃至全世界,有更多的人来了解汉语、学习汉语、爱上汉语。
记
者
手
记
他给儿子取名叫做“迅”
在见到内田庆市教授前,就听他的中国弟子介绍:“内田先生非常儒雅,衣着打扮永远一丝不苟。”原本以为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者,等见面交流后,才知道什么是“君子如玉,触手也温”。
采访前,我们先听了一场他关于文化交涉学的讲座。整个讲座用中文进行,那些独特的发现和视角,常常引得现场听众有醍醐灌顶之感。
讲座结束后,内田庆市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交流中可以看出他对汉语的专注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比如,他喜欢鲁迅,因此给儿子取名“迅”,以此向这位中国先贤表达尊敬和纪念;为了研究汉语,数十年来他利用在世界各地进行学术交流的间隙,去搜集、寻找资料,至今已有3万多册有关东西方语言接触史的图书、资料等珍贵文献。在自己研究的同时,他还将其中的珍本、善本书籍影印出版,使整个学界受益。退休后,他又将这些资料全部捐赠给日本爱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作为内田庆市相交多年的挚友,曾援引拉丁语格言“Reges grammaticis non imperant”(帝王威仪难匹语法权威)来诠释这位学者的精神品格。在李雪涛看来,不管是在汉语语法研究以及文化交涉学、文化翻译等领域,还是对生活的热爱上,内田先生的深厚造诣与饱满情怀,都为文化的延续和传播奠定了基础,这种价值超越了世俗的权力。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七十二期
执行:杨昕
记者:王国平
摄影:李强
海报:刘津余
编辑:梁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