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庆胜 铎文
别林斯基说,对一部作品的评判,首先应该考虑它“是不是艺术”,然后再看它表达的社会思想。因此,对一部散文集的学术评判定位,首先应辨明它是不是艺术,在艺术上提升到什么程度,否则不关注艺术本身,仅连篇累牍地重复人人皆能说会道的社会思想性,这种评判定位就严重偏离了散文集评判的最重要功能。深层阅读沈俊峰的散文集《影子灯》,感到他的写意散文艺术突破非常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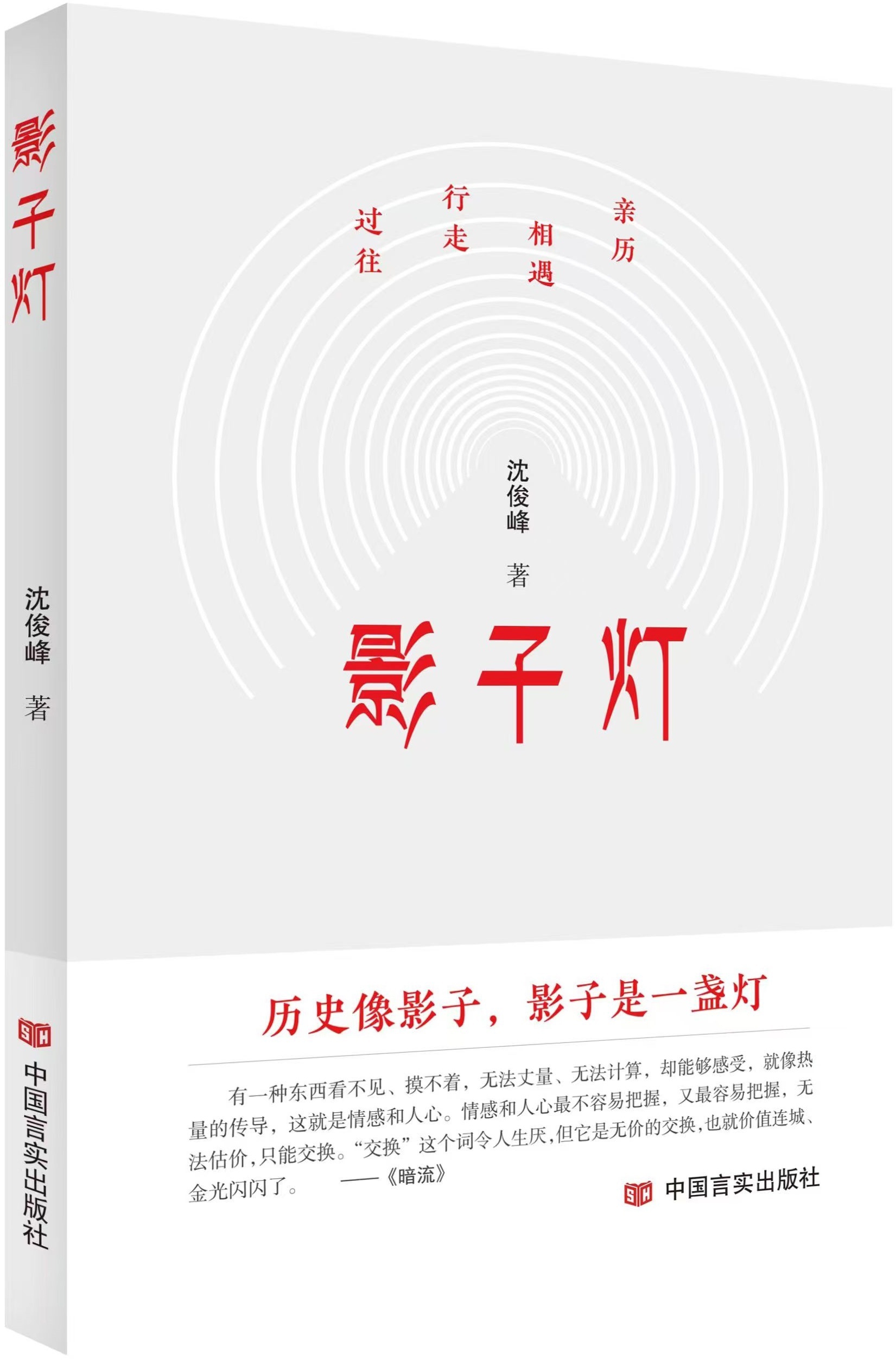
什么是艺术?对艺术的本质内涵,英国视觉、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美学家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中译为克奈夫·贝尔)认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也就是说,必须具备特殊的“有意味的形式”才是艺术,否则就是一般的交流生活的信息。这就是艺术语言和一般交流媒介语言的根本区别。
《影子灯》的语句“有意味”:“时间就像一场不怀好意的大雪,填沟塞壑,愈合自然伤口,覆平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我们都知道,“时间”只是计量时辰的一般外物,没有思维,但沈俊峰却艺术化地把“时间”比作是“一场不怀好意的大雪,填沟塞壑”,并且“愈合自然伤口”。在这里,“时间”成了艺术特殊物,转换出作家特殊的主观意味与社会“意味”了。
同理,我们见到的自然界的“日子”也只是一般外物,也没有思维,但沈俊峰笔下的“日子”,“真像落满一地的黄叶。秋意饱涨或萧飒,等待春的来临。”这“日子”也成艺术特殊物了,也转换出散文作家特殊的主观意味与社会“意味”了。
合肥是安徽的省会,但在沈俊峰笔下,合肥却成了“一个非常寒酸的小家碧玉,梳着两根短辫子,穿一双平底鞋,相貌平平,见人脸就红”,这是多么的“有意味”。这就是写意化艺术的审美创造。
那么,我们司空见惯的“黑夜”呢?沈俊峰认为:“因为这静,我才感觉到夜是那么真实,真实得我可以触摸到她的肌肤,感受到她的气息。”更写意地创造道:“忽地明白,原来,黑夜是为了让光明喘口气;原来,黑夜是光明的一座加油站,让光明休养生息。如此,光明才会更洁白、更纯净、更透明吧!”
如此写意艺术审美的创造,还有:“这是一条汹涌的没有心的河流。河流裹挟着泥沙和我们,茫然向前。”“没有心,就没有爱,更没有慈悲。即使看上去像有爱的模样,也不会具有爱的温度。就像一对演戏的情侣,将激情进行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中间却隔着一块不易察觉的透明玻璃……”
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的是,这种普通“外物”的新型艺术逻辑自觉发现功能,只有优秀的散文作家、艺术家才能具备。茵格尔顿曾有一个很具重量级的美学价值判断:“被审美感知的自然具有本质上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只要它美,必然会有被审美感知的可能。从艺术审美意义上观照,世界上的任何物件,哪怕一个微小的沙粒、一段草屑、一根枯枝等,都具有多样的艺术审美意义,这就要看遇到的主体是否是美学家、艺术家、作家。
美国美学家格式塔心理学派创始人阿恩海姆,曾发现事物之间的“完形”式、“同形同构”或“异质同构”的美学关系,比茵格尔顿的美学阐释更前进了一大步。也就是说,必须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在某一点上达成一致,这种碰撞才会出现,这种“必然”联系方能形成,这就是诗人与世俗个体思维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最根本的区分素养在于能不能进行艺术转换。
对于艺术散文的学术判定,有不少大家涉猎过。他们都强调艺术散文在某一个方向上的、自己认为最主要的特征,其合理性是明显的,更是他们艺术成功的个性经验总结。这些界定不矛盾,但的确给人松散之感,更说不上是共同语言,这就给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充分暴露了“散文”没有明显特征的严重缺陷,就像撒了一地的豆子,“不矛盾”地各自沿着自己的“力”的方向滚动。
哪一种“滚动”更好?真是令人怀疑。或许正是因为用“力”方向不一样,学术界才有了杨朔的“卒章显志”式,巴金的“说真话”式,冰心的“冥想”式,孙犁的“本色”式,贾平凹的“乡土风情”式,更有余秋雨几乎异口同声褒扬的“学者大文化”式等理性分野。
这似乎又给了我们另一种更重要的学术与创作启示:艺术散文要想出彩,就要有意识地强化写意而有新的实质性突破,这可能就是散文的最美好前途。
(《影子灯》,沈俊峰著,中国言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