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树
尘土与大地有多少种交汇的姿态?如果以微尘喻人生,它要经历怎样的翻飞升沉,才会最终回归大地的怀抱?而这回归又是否是必然?在大与小、永恒与瞬息的对比之间,我们该以何种笔触,书写微尘经行的轨迹?翻开凌仕江的散文集《微尘大地》之前,它的标题带给人无限涣漫的遐思;读罢全书,充溢心间的则是酸楚的温暖。
凌仕江在这部新作的40篇散文中,写人、写花,写蝉鸣蛙叫、故乡他乡,更写行走在人间热土上的惶惑与赤忱、与人生旅伴相别相拥的苦痛与温情。它是个体经验的诚实记录,也是对寄寓天地间如微尘般飞舞不息的生命们的讴歌。
以字数论,《微尘大地》算不上什么大部头;但阅读它却颇费了些时间。我总是读一阵就得停下来,缓缓神,喘口气,任由随文字翻涌的思绪慢慢平复。并不是它的文字多么难懂,而是文字里的“坎儿”太多,情绪的、词语的、观念的……它的质感绝非丝滑甜美,反而沟壑纵横、扬沙飞土。但在迷眼烟尘落定后,它给出的,又是一种躺在故园土地上的宁静与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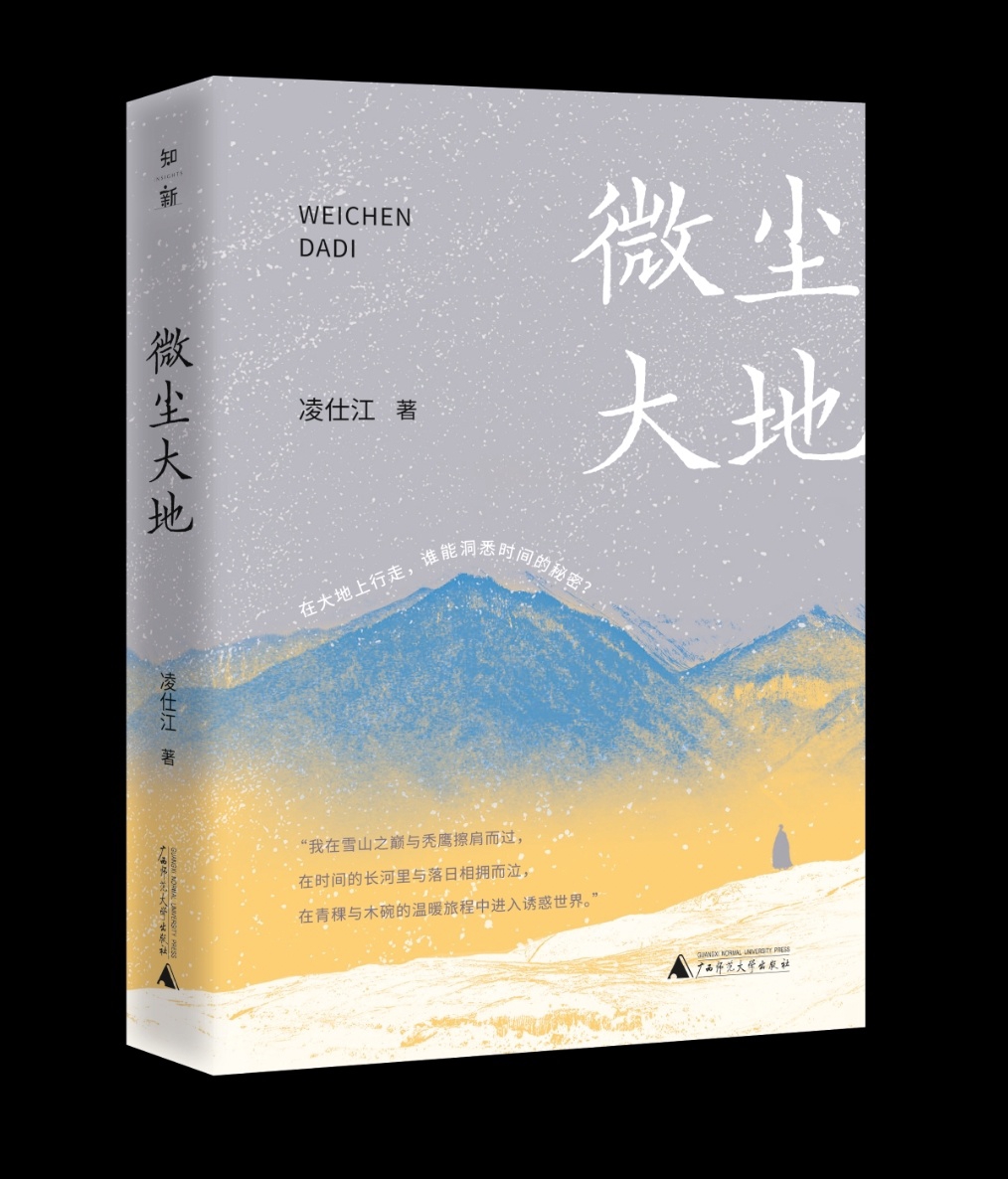
全书一开篇,《花隐谷》便道出了一种今日人人共有却又难以言说的愁绪。在钢筋水泥森林间忙碌的人们无暇赏花,而落寞在老屋与故乡的父母辈,他们的春天业已寂静。花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了,这并非物理上的消隐,而是像花一样生机勃勃、带着山林水泽之气的乡村生活,人与人、人与家乡还凭着肉身的真切知觉相触摸的时代,已在精神上被动地退场了。
“我的抱愧,皆因错过那些芬芳生命匆匆而逝的花期。”然而,“如今,回到故乡总是寸步难行,我知道无论我把脚延伸到哪儿,多的是花,最难看见的是人。”并不长的文字中,几回转折,几番顿挫——对花,我们有一番辜负芳期的抱愧。对故乡呢?对无缘再见、星散各地的乡人们呢?而之于滚滚向前的时代,每个人、每代人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同花一样“纷纷开且落”?
于是最后,峰回路转般,作者给出了一个略显俏皮的结尾:“做一件不厌其烦的事:给故乡的每一座山坡坡、每一条水沟沟、每一朵花取一个好听的名字。我给老屋取名——花隐谷。”在怀念与怅惘、在隔膜与迷茫后,他选择的是铭记与重新书写。给事物取名,就与它结了缘。即使已不再是稚童年岁,人依然可以选择坚持一份天真,与或许终会消失但此刻真切存在的一切结缘。
开篇写中年况味,无暇看花,有满面风尘之感,结尾却归于这样干净的喜悦。它并非生命伊始那种无知无觉的纯净,而是遍历世事后仍愿回返最初的、泥沙澄去后的澄澈——这正是自《花隐谷》起浸润全书的气质。作者有足够的敏锐捕捉浮动在空气中的焦虑与狼狈,又以足够的诚实接纳消化它们,如同大地张开怀抱,耐心等待微尘在狂舞后静静下落。
继续读下去,我结识了许许多多素昧平生的人们:羞怯地等待出嫁却迎来一场灾难的三姐,陷在城里的哥,害怕被斑鸠喊魂的老人,“鸭司令”舅舅,得了哑症的练孃孃,老实却精明的二莽,死于异乡的年轻人……他们在文字中那样确凿、鲜明、不可抗拒地浮现出来,带着我不完全能听懂的声腔,传递着独属于某片土地的记忆。他们不容被草率地评价,因为作者把镜头拉得如此之近,近到看得见三姐期待出嫁时鞭炮的烟雾,听得见二莽背着父亲求医时喘的粗气,在细致到纤毫毕现的描写中,作者的情绪分明满溢,却不曾决堤。
呼唤出走的游子时,他写母亲的深情:“母亲说的,吃鸡蛋是图个圆。然而,鸡蛋下肚之后,家就像鸡蛋裂成两半,一半在城市泛白,一半在乡下泛黄。”朴素的比喻如同离家时母亲的叮咛;然而,他又深深懂得游子无处安放的野望:“所有出走者都因为村子的沦陷而无法看见膨胀的城市。”他想将父母接进城里的荣誉,在残棋一般的家园面前,永远面目模糊,永远得失难计,永远晦涩如加上了太多修饰词的文字。
在《微尘大地》中,流动的既不是自顾自追忆过去的田园牧歌,也不是置身事外、居高临下的责人宽己。不如说,从头到尾,作者只是在真诚地困惑和迷茫。他写从小到大都为称呼犯难,为故乡老气横秋的语序定义而不适。但当人到中年回乡,从言语到行为都难以协调、曾相称呼的人都已老去或离开时,又有由衷的悲凉。故乡,故人,他人,自己,谁能肩负起全部的责任,谁能全错或是全对?
作者无意于作粗暴的判断,他给出的只是文学所能做到的全部:诚实。而这正是它的感人之处。即使作为后生读者,书中所写人事许多已经于我十分遥远,但我仍会为那种夹在过去与未来、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茫然与眷恋,在某一刻忍不住眼角泛泪。
自然,乡人乡情不是《微尘大地》的全部。一页页翻过去,你会忍不住惊叹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之细,遐思之远。任何平日不加留意的事物,都能成为他飞扬思绪的起点,延伸出万缕千丝,与旧时光里的某个少年曲折相会。
他写寥落成景观的杂志铺,渐行渐远的是一代人的纸上文学历程;《蝉自故乡来》《竹象飞舞》《与蛙共鸣》里,“死心塌地趴在窗上的蝉”、未曾听过的“笋儿蛆”、在城市中为疲惫人群带来一个池塘故梦的蛙,在字里行间鲜活着,如同有情众生在互相致意;写人间草木,从无声无息开遍身边却不察觉而抱愧的樱花,到昭觉寺里静默的蜡梅,无香艳烈的海棠,与爱情同步枯萎的风信子,一茬茬花期,一段段流年,就这样开而复落;地方在书中更不是苍白的,它们有声有色,建昌空气里的滇红茶香、简阳饭桌上的毛鸭子、茶马古道的鸽子花,色彩、声音、气味攀援而上,如同爬山虎爬满墙面般,直伸到读者的眼前、鼻端。
在这场纸上的旅行,最可靠的向导无疑是作者的文字:时而精警有力,时而绵软多情,时而静默地燃烧。
《被词语追杀》一篇,起手将词语比作杀手和不请自来的投宿客,令人悚然一惊,又在回味后不得不点头:我们和词语的关系不正是如此吗?有时我们疲于奔命想要逃脱的,岂非正是一个道出了真相,而令我们难以承受的词语?作者冷静地分剖着字眼:“‘肥胖’原本是个很不结实的词语,却能勾起越来越多人对它实实在在的恐惧和警惕。”经这么一提醒,我顿时觉得“肥胖”二字的质感确实是软的,仿佛要流动的,然而,那油脂的堆积又给人喘不过气的窒息感。
在写相对抽象的内容时,作者也会引入生活化的譬喻,让文字在生动中又有一分对世情的悲悯:“一发不可收的词语,闯进相同的世界,总有打不完的架,就像命不好的母亲,打同样命不好的女儿。”读时唯有苦笑,为词,为人,为这进退维谷的一生。
对文字的敏锐觉察,贯穿《微尘大地》全书。写蜡梅时,作者对“腊梅”和“蜡梅”两种叫法颇费了一番斟酌:“腊”与“梅”一结合,似乎已带着岁月与死亡的暗示;而“蜡”则更倾向于超然与内敛。二者虽然都是重量型的字,但前者是节气轮转,后者则指向梅魂永生。这的确是对文字、对生命极其用心去体察的人,才能咀嚼出的微妙差别。“蜡”有光滑微冷、不衰不朽,近于无机的质感,它让我想起古代的一种香料“返魂梅”,将梅花入香,与将梅花覆上一层“蜡”的文字保护膜,同样是为了留住这一缕香魂吧?
更多的时候,文字里浸润的是作者对世间的一番深情。他写什么,就随着摹写叙述的对象转换口吻声腔,让它们经由自己的笔,被引渡到另一个时空里来。
写乡村时,他用梦呓般的调子,说“稀饭绝对不能原谅干饭”,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一时难以索解,却又不是真的不解。这话是不能念的,要轻轻地用近乎唱的腔调,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口口相传;写及景物时则多用灵动笔法,“绿叶沙响”“月光雀斑”“枯萎燃烧”“春芽缠绕”,生命在其中起舞回旋,扬起的裙摆便是文字的末梢;写及人情时则以一个个简短有力的比喻,“往事成痂”,伤痛褪色而不灭,“隔音板那头迎接我的不只是暴风,肯定还有骤雨”,情绪如有实体,山雨欲来。
把这300多页的路走完,重新看向《微尘大地》的书名,不由得一叹:好贴切。书中所写,并无壮阔的事业,也没有足够跌宕的情节,有的只是如微尘般曾经飞舞而终将落下的卑微生命。在时代的洪流中,在时间的磨蚀下,它们显得何其渺小,如同一树花在无人注目中走过盛放到凋零的全程。
然而,微尘的悲凉,最终归于大地的温暖。生命固然短暂无常,而寄寓天地间的一遭,终究交织出了许许多多故事,为眼眸和文字封存。微尘的舞动,之于天地只是短短一瞬,但人间的种种悲欢、无限心事,不也正是在这交会的一瞬发生的吗?
至此,《微尘大地》的用心与价值,便显露无遗了:尽管渺小,尽管徒劳,但每一粒微尘,都在以其落下前的飞舞,丰富厚土承载的深度。注视它,感受它,在落下前记录它,这便是人能对生命所作的,最高的礼赞。
(《微尘大地》,凌仕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