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在线记者张斌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这是唐代杜甫描写的成都音乐盛景。
那么,成都的音乐文化起源于何时?在鼎盛的汉唐时期又呈现怎样的特点?4月19日,考古学者、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霍巍以“汉唐成都与丝路乐舞”为题,在成都博物馆与观众分享,重现一座“国际音乐之都”的灿烂往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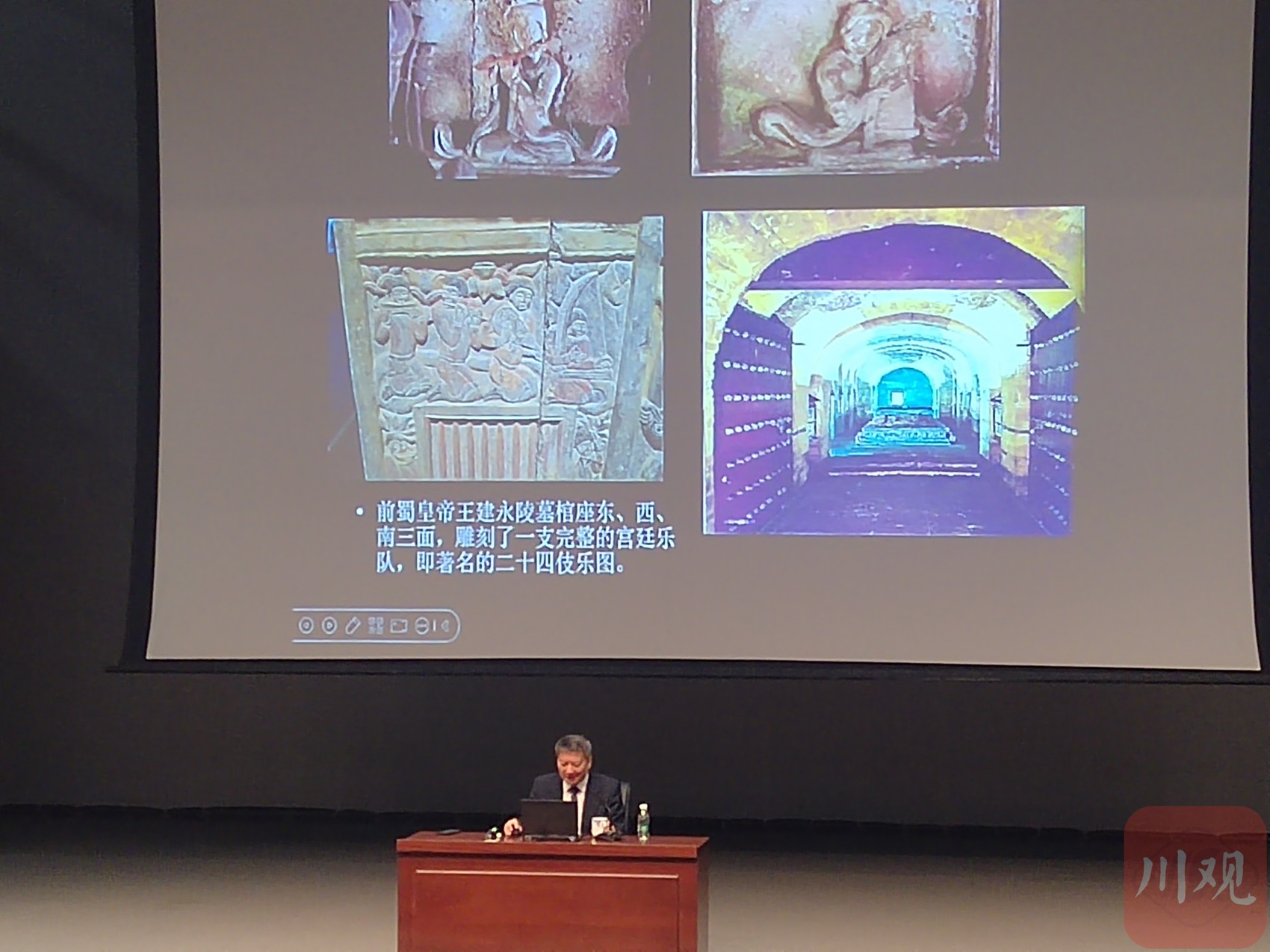
霍巍讲座时的情景。张斌摄
青铜时代
不仅有祭祀的庙堂音乐,也有民间的巴渝舞
在成都平原,距离汉唐时期的成都最近且规模最大的考古遗址当属三星堆遗址。霍巍首先以一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坛”说起。
这件文物底座上有四个力士,四面有四个小象,他们肩负着上面的神坛,而中间坐着一个小人。这个小人并非普通人,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坐姿,所以它更可能是神。而在力士的上层,站立着一只只铜兽,它们张开梯形大口,踩在力士的肩膀上。铜兽驮负着一个铜人,铜人手上托着一只鸟足铜人,他手持玉璋,仿佛进行一场遥远而神秘的祭祀活动。“在祭祀过程中,难道他们始终保持沉默吗?祭祀活动是否应该有音乐相伴呢?”霍巍随即引出话题。
关于上述问题,霍巍给出肯定解释。他介绍,考古学者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均发现了石磬。这表明,他们在祭祀时很可能是要演奏音乐的。“而这种音乐就是我们所说的庙堂之曲,即祭祀使用的音乐,这已经是一种相当高级的音乐形式。”
而放眼文献中找寻巴蜀地区音乐的历史踪迹,则呈现出另外一条线索。《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这表明商周时期,巴人参与了周王讨伐殷商的战斗。开战之际,他们齐声高歌,以舞蹈为号,用舞蹈激发力量,鼓动士气,舞动起来,气势逼人,威震四方。
此后,无论是文献记载中汉高帝灭秦过程中“巴渝舞”的再次活跃,还是民间俗语“下里巴人”的流传,都显示出巴蜀大地上有一支充满活力的民间音乐舞蹈,而且,巴渝地区的音乐还传播到长江中游一带。
霍巍强调,尽管考古工作者目前尚未在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青铜时代的大型编钟、镈钟等乐器,但在三星堆、金沙发现了许多青铜铃铛,这些铃铛可能被悬挂在参与祭祀的某些礼器上使用。“虽然发声的石磬和青铜铃铛不足以构成早期成都音乐的全貌,但是,都可能是当时三星堆人举行祭祀时留下的音乐遗存。”
同时,从此后出土的一些器物反推三星堆、金沙时期的音乐状况。例如,在四川茂县牟托石棺葬中出土过编钟,而该石棺葬可能是三星堆-金沙发展到后一阶段,有一支古蜀人族群回迁到祖先发祥地。“它不仅体现了青铜时代中原礼乐文化的特点,还带有一些鲜明的巴蜀地域色彩。”
此外,出土于巴蜀地区的乐器虎钮錞于,既反映了巴蜀地区的图腾崇拜,也是这一地区青铜时代音乐文化的有力佐证。
汉至魏晋时期
本土俳优俑、外来胡人俑展现了音乐繁荣
而关于汉至魏晋时期的成都音乐发展,霍巍同样从三星堆讲起。
他介绍,在新一轮三星堆考古中,学者们发现了三星堆碳化丝绸残片与编织经纬的显微证据,则揭示了古蜀先民精湛的丝绸技艺。而这一发现,引发学者对成都平原早期远程贸易的思考——三星堆人有没有可能将丝绸输往域外?
而他引入文献记载,公元前139年,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一带)发现蜀布、邛竹杖等物,据《史记》记载,这些物资经“东南身毒国”(印度)中转而来。经过考证,霍巍认为,“蜀布”极可能源自三星堆延续的丝绸业,这也印证了古蜀与南亚、中亚存在可能的贸易网络。
霍巍介绍,随着丝路贸易的延伸,多元文化也在巴蜀大地激荡。如四川出土的东汉至三国的一些陶俑,常见高鼻深目、头戴尖帽的胡人乐队形象,他们或奏异域乐器,或联袂起舞。而郪江崖墓M3墓室中的彩绘胡人尤为典型。他们身着紧身衣、足蹬长靴,留着络腮胡,展现出鲜明的异域特征。“这些胡人不仅作为丧葬仪式的参与者,而且被纳入到墓葬体系,更成为音乐传播的活态载体。”
霍巍特别提醒,胡乐传播还与佛教东渐形成合力——如乐山麻浩崖墓的东汉佛教造像、成都平原及周边发现摇钱树上的西域幻术形象,均显示了佛教传入,也将域外的艺术与音乐带入了成都及周边。
在受外来音乐影响的同时,成都及周边地区还保留了自身音乐文化特色,如考古发掘中大量涌现的俳优俑,“不仅保留了本土人物形象,还传递出乐天知命的音乐文化。”霍巍表示。
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促使文化通道转移。当鲜卑政权阻断北方丝路时,僧侣商队改行“青海道”,沿长江经成都西入青藏,再折向西域。这条迂回路线使成都成为佛教艺术中转站:成都西北方向出土的褒衣博带式佛像,具有鲜明的南朝士族服饰特征;而护法狮舞与天马形象的出现,则彰显域外艺术的融合。
唐代
丝路鼎盛与音乐集成的巅峰
隋唐时期,成都依托“扬一益二”的枢纽地位,迎来城市与音乐文化的双重蜕变。
霍巍介绍,此时成都摩诃池园林区的形成,营造出“水榭笙歌”的盛景;而“陵阳公样”蜀锦的诞生,更像是一场跨国共创。
随着敦煌与成都定制丝绸贸易的兴盛,音乐交流亦更趋频繁:巴中、安岳等地的石窟中,长安样式与于阗元素共存的飞天乐伎,见证着佛教艺术的东西汇流;而瓷器、香料、珠宝贸易带来的波斯商人,也使成都街头出现“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现象。
他介绍,唐代音乐集前代之大成,形成空前开放的体系:太常寺管理的宫廷雅乐延续周礼传统;秦汉以来的新声清乐则在文人中流行;龟兹乐主导的燕乐经西凉乐调和后风靡宫廷;而“胡部新声”则吸纳粟特琵琶、波斯箜篌等外来乐器。
在霍巍看来,当上述的时代的多元性传到成都,则在前蜀王建墓的二十四伎乐浮雕中得到集中体现——乐队列东西两厢,既有笙、筝等中原乐器,亦见竖箜篌、答腊鼓等异域器乐,羯鼓与钹的搭配更凸显胡汉合璧特色。
例举唐代成都音乐的空前繁荣景象,霍巍认为,这是丝绸之路文化积淀的大爆发,“以丝绸为载体实现了艺术的跨文明传播,也与成都的交通枢纽地位以及文化熔炉效应密不可分。”霍巍强调,这种多维度的交流最终促成了“锦城丝管日纷纷”文化现象的产生,也为中华音乐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