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莹莹
在汗牛充栋的苏轼传本中,沈荣均的《苏东坡的理想国》以三重破局的姿态,开辟了东坡文化的新版图:首先是通过双向互补的学术架构与前人传记形成思辨对话,二是以风物志和地理书写解码苏东坡的精神原乡,三是以俯瞰历史的恢弘视角重构北宋士大夫的集体困境。全书沿着“归去来兮”的返乡路径,在诗意审美和历史纵深间,呈现出独特的结构性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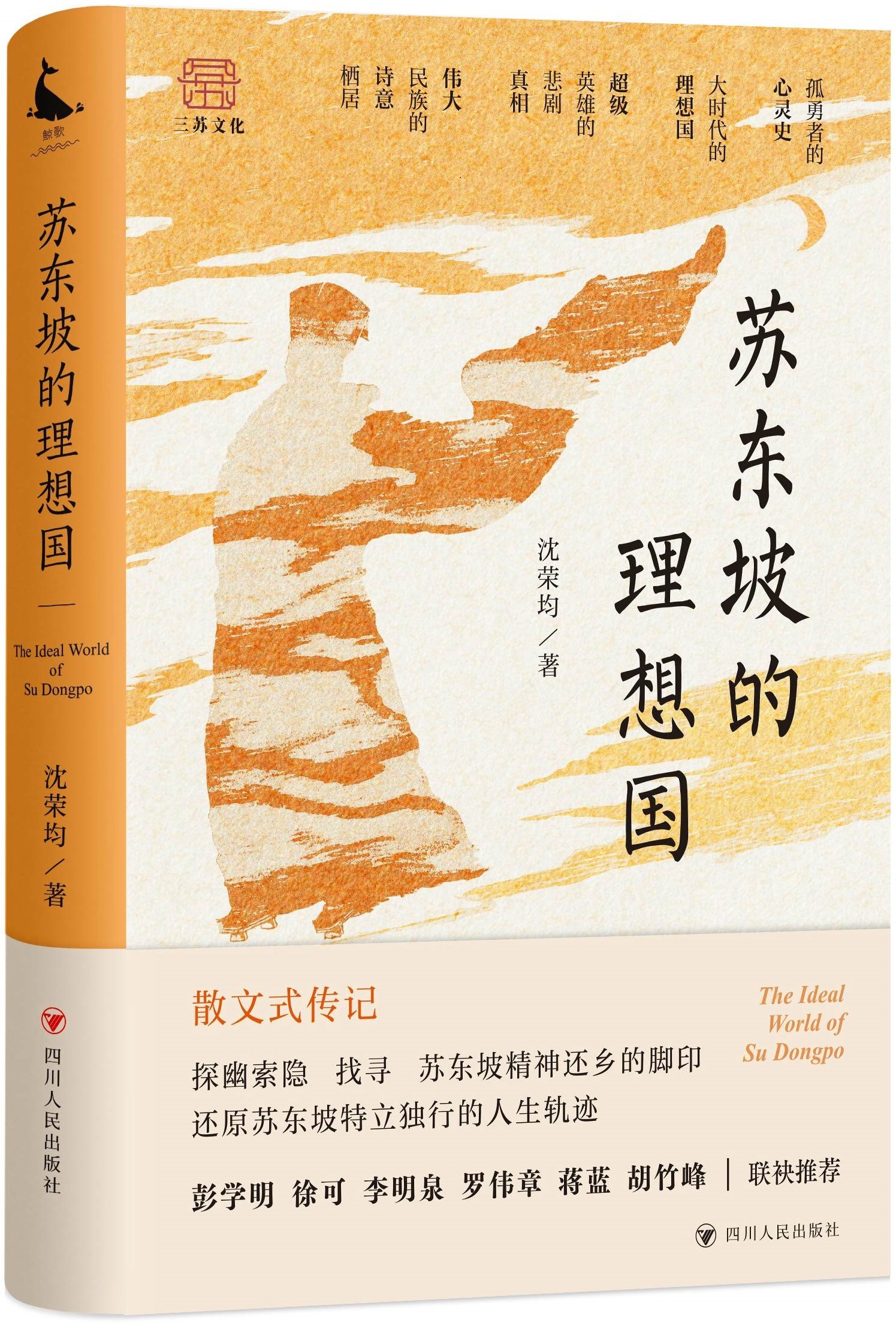
学术纬度的破界:互补而非对立
一是叙述破界。
沈荣均的文本叙述参照了年谱时序,嵌入和勾连部分就像古本中的眉批侧批,双行夹批。随着文献综述的加入,尤其对符号的创造性应用彰显出独特的评论气质。
例如“二程”学说因为符号崇拜而陷入纯粹抽象的局限,但苏轼长期在基层,他的符号是“桤木”“巢菜”“猪肉”“墨竹”“仇石”等民间应用的实物。于是,在苏轼踏足的地方,都有类似的符号伴随,或者留存下来进入新的叙述空间,如此拆解了传统历史书写的线性桎梏。
二是学术破界。
基于国学大师对宋文化的痴迷,以及欧美和日本汉学家将宋朝作为历史比较的范本,沈荣均指出,林语堂的精神造像,李一冰的生命复刻,和梁启超演绎王安石一样,都有“单向救治”和“双向完善”的局限,也都是作者自己的主义。这种学术自觉,在理想主义者、士大夫的行动性等章节里展现为立场的超越。
例如,借京都学派“新法具社会主义性(宫崎市定评语)”讲述王安石变法的现代性基因,又以苏轼上书《谏买浙灯状》,释放关押百姓等细节,还原“政虽无术,心则在民”的底层逻辑。
在将王安石与苏轼的理想差异进行比较时,作者展现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前者秉持“逻辑崇拜者”的制度信仰,后者践行抚摸式治理的“温暖包浆”,从人格冲突到理想互补的认知跃迁,使王安石变法的辩证解读,跳脱出传统的派系二分法。
三是策略破界。
沈荣均认为,苏东坡是集体缔造的信仰,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典籍作为宗室墓志铭存在时,也有对士大夫人格标签的注解。
例如,章惇是奸臣,南宋和元代史学家对此毫无争议,但有近代研究者持不同看法。沈荣均让苏东坡走下神坛,证实真理一样的抽象完人并不存在,还证明了苏东坡之所以伟大,并不需要拉低他人来烘托。真实的苏轼比神坛上供奉的苏东坡,更有力量,且生生不息。
这种实验性写作策略,有可能触发读者对当代历史传本的重新评估。假如历史的尘埃可以在诗性正义中获得重构,那么,真实理性的文本或许要在解构来临前更完善。
物质故土的转码:物象即心象
一是故乡转码。
在东坡研究逐渐成为显学时,研究本身也陷入重复阐释的困境。沈荣均用“诗史互证”的散文笔法实现创新,将东坡文化所涉的历史、地理、书法、绘画,与他构筑的东坡叙述相呼应,调门在故乡眉州,经过搅拌、黏合、酝酿、发酵,成为东坡文化的眉山腔调。其中的历史考证与诗学阐释相互交织,既不同于学术圈层严谨枯燥的考据堆积,又脱离了大众读物浅表化的圣人景观,呈现出学者型知识储备与诗人型审美感知交融自冶的写作范式。
实体眉州的文化名人和地标,聚焦在三苏祠下,故乡至此成为苏轼认识世界的起点。从眉山短松冈到杭州万松岭,从凤翔喜雨亭到密州超然台,从徐州放鹤亭到惠州白鹤居,西湖、独山、仇池、雪堂、赤壁、潮阳复古桥、儋州桄榔庵、郏县小峨眉,物质故乡的动态化叠加和过程化转码,形成东坡精神诗意栖居的“无何有之乡”。
二是物象心象。
在沈荣均的东坡叙述中,曾经作为学术标签的地方神灵、方言符号、饮食器具,甚至《西园雅集图》里竹节拐杖的微观呈现,都形成了细小而真实的历史触须。沈荣均的散文功力在此大放异彩,将重若千钧的精神命题在山林桤木、假山怪石、白鱼紫笋和躬耕烹煮中,完成从物象到心象的转换,让我们窥见传统学问突围的另一种可能。
以“宋四家”的鉴赏为例,沈荣均写“《寒食帖》像个严重风湿肩周炎的老年患者”“《松风阁诗帖》昂首踢腿,一律闪了腰地喊疼”“《吴江舟中诗卷》右伸左缩”,需要读者心中的拐杖支撑。“颠倒、不安、扭结,颠覆了均整、安定、和谐的美学”“书生们守着‘蔡’的中规中矩,又为‘苏、黄、米’的歪瓜裂枣嗟呀喝彩。”这些自然表述,不失审美意趣,精准传达了宋代读书人“在完善中抗争,在抗争中权宜”的心象描写。
三是精神返乡。
沈荣均洞见,理想知识分子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又是现实困局的介入者。于是,从开篇就涂抹着“故乡”的文学底色,伴随研究纵向深入,到“形而上的山水”篇里锋芒毕现。
黄州东坡创世命名,苏轼却已形如枯木。他一头挑着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另一头挑着司马光的元祐更化,延宕至“归去来兮”的终章,借助陶渊明的桃源哲思,将知识分子的理想求索演绎成诗意地栖居,作为20世纪伟大而深刻的命题。
沈荣均通篇都在进行东坡文化基因的溯源与重组,眉山苏轼也因此不断叠加,完成从物质故土到心灵原乡的终极跨越。例如,青年苏轼启程离乡,直到黄庭坚寻至眉州,看到与“霜髯三老”的荔枝约定,这段描述让苏东坡的返乡之路充满张力。
又如,他在杭州“留诗四百七十四首(苏辙)”,是用文墨构筑理想的乌托邦;创设安乐坊、疏浚六井,则是将理想照进生活的现场。“知行交互”的返乡模式,与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新法,共同推动着宋代文明的进步。
王安石试图以变法重构制度家园,苏轼便再造生活安身立命,通过上书《谏买浙灯状》、释放关押百姓等细节,证实苏轼的批判从来“不是派系的枪,而是时代的枪”。这种超越立场的发声,恰是知识分子最本真的精神还乡。
“乌台”一章里,在读者急于求解真相与黑暗突围时,沈荣均却用两节篇幅流连于佛相庄严。他讲东坡竹,文与可,讲士人画,东坡立笠,这些植物秉性恰是读书人的草木精神,是作为政治对手的不合作存在。
人生如草木,一枯一荣都应对着知识分子的精神返乡。
历史观照的纵深:乌台困局的史鉴
一是多层悖论的肇因。
写苏东坡,绕不开的是乌台诗案。对其真相的还原,沈荣均采用布莱希特“打破第四堵墙”的方式,剥离了苏轼的神圣光环,将这场文字诏狱还原为历史空间里的人性悲剧。
乌台诗案起因是苏轼的诗文被利用,神宗皇帝企图借整顿言论重塑变法权威,御史台官僚则试图通过构陷建立政治资本,而苏轼在立言传统和为民请命中陷入修辞困境。多层肇因叠加,与其说造成苏轼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庆历新政以来北宋士大夫集体困局的爆发性呈现。
这场文字诏狱的微妙之处,就在元丰这个时间点,知识权力的迭代临界正好抵达。活字印刷技术的革新,使苏轼的诗文传播突破地域限制,上达天听的同时,还持续解构当权者的话语体系。这种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正在成为某种深刻影响社会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强大工具。”不仅北宋官僚系统尚未适应,就连苏轼也没意识到,自《诗经》以来,士大夫赖以安身立命的立言传统,面临着传播方式的巨大挑战。
沈荣均研究强调,御史台的定罪逻辑,本质是对新型文明秩序的陌生与恐惧。因为认知盲区的原因,诏狱的当事各方“共同构陷了一个文化史的巨大黑洞”。
二是穿越文本的叩问。
走近东坡研究的学者,最终都会进入元典溯源学术传承的象牙塔。沈荣均没有止步于东坡个案的文学分析,以历史的眼光连接了王安石变法与明治维新、新文化运动等宏大命题。
王安石变法“主张经学(理念)先行,经验(实践)护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都是有人先知先觉,推动纲领性东西出台,由某个先进政党群体游说天下,然后才得以扫清意识形态障碍,获取广泛民意支持。”因此,沈荣均对乌台诗案的诠释突破传统政争视角,转而关注活字印刷这一媒介革命如何重构社会话语体系。
新时代文化映照:一滴水可见太阳
一是当代性的悄然介入。
首先是文本叙述的人民性。如描述杭州众多东坡遗迹,还有偶尔出现的“犟拐拐”“方脑壳”等方言口语,一边消解着散文诗话的腔调感,一边像撒胡椒面佐饰东坡文化的民本思想。
其次是对当代苏轼研究的注解。例如,内山精也分析乌台诗案时认为,活字印刷的应用超出了王朝知识分子阶层的认知,沈荣均指出,这本质上是一场言论管控的危机。
第三是文化符号的当代应用。“东坡风物志”里,有一处“东坡金城”房产项目的插入,看似突兀,实则需要承受历史的检验。开发商将东坡故里的符号切割成商品地标,书香城市的家教狂欢构成物质时代吊诡的黑色幽默。
二是新时代的文化赋能。
在“归去来兮”的终章,沈荣均明确了整部作品的主题写作动机。他肯定王安石变法的系统性和前瞻性,以新世纪、新时代的全新视野,总结和反思王安石变法,并以此致敬从古到今,指引国家发展改革的知识分子。
因为主题写作的动机,沈荣均以眉山本土东坡后学的姿态,在“眉州好学”篇里堆砌文化地标,掘地三尺穷尽眉州的历史文化名人为他们树碑立传。可以肯定的是,沈荣均创作苏轼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由此产生的文学成就、人格魅力和人生哲学,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滴水照见太阳”是现世的关怀,在沈荣均叙述的理想国里,苏东坡的草木文心就在历史的褶皱里,一生向阳。
(《苏东坡的理想国》,沈荣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