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燕
“她看向远处的山峰,忽然觉得山又不像海浪了,倒像是一条条毛茸茸的大狗,披着厚实的皮大衣。有些狗蜷着身子睡觉,有些狗低着头喝水,有些狗则抬着头望天。”这是余闲的儿童生命教育小说《小云兜里的梦》第一章里,主角龙小云在上学路上对山峰想象的一段描述,形象而不失童趣,直接而不乏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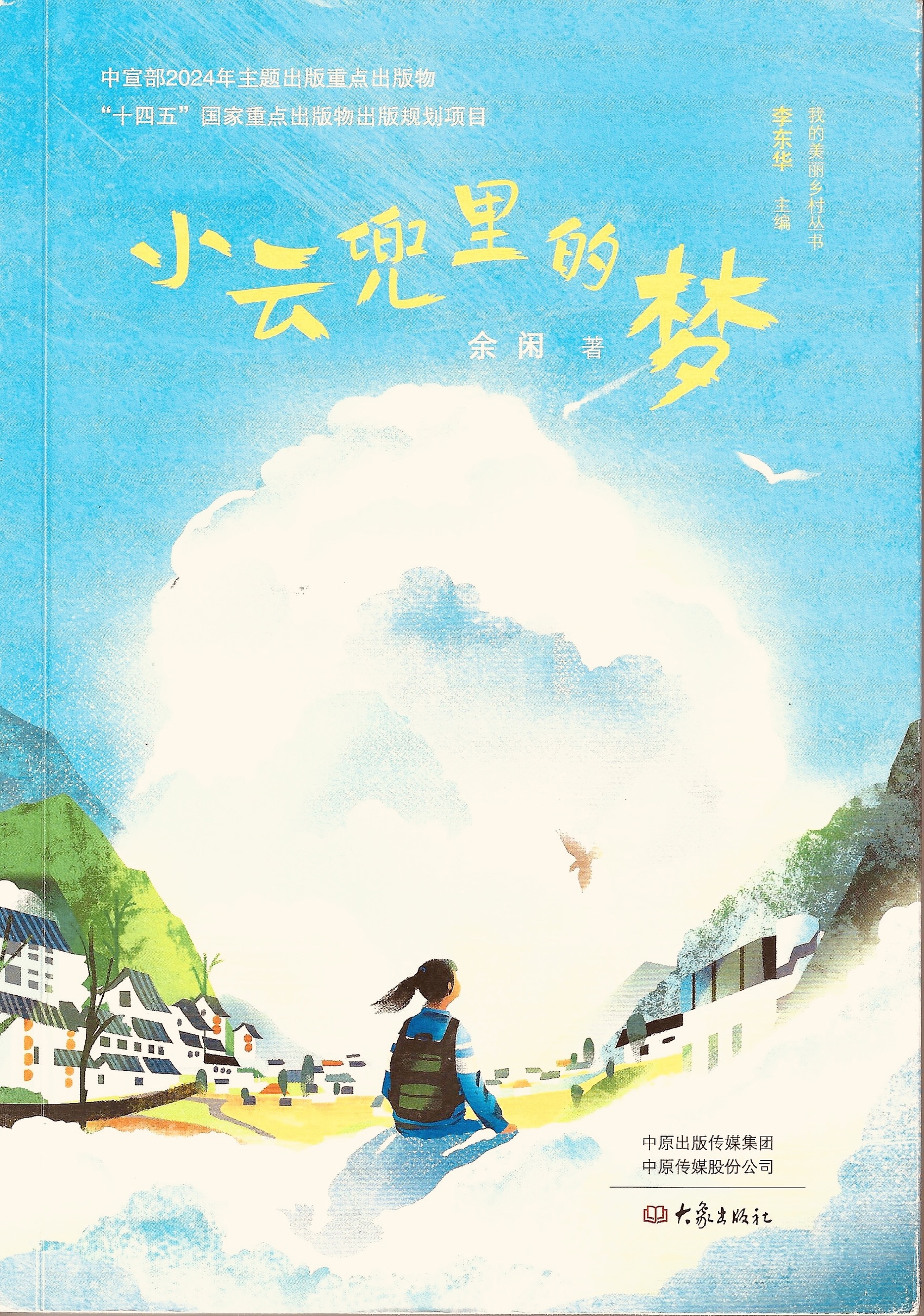
20年来,余闲一直在生命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创作路上努力。《小云兜里的梦》,是他对个人经历、儿童与时代关系的一次创意写作的探索性回答。
AI时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新要求:灵性思维和情感共鸣的内核呵护
大模型3秒写出满分作文,AI绘画软件轻松生成手抄报,智能音箱张口就能讲睡前故事……AI时代,儿童的学习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对儿童文学创作提出新要求,即一边要接受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日益紧密共生的现实趋势,一边也要维护儿童成长发展的核心能力。
有报告显示,每天自主阅读超过30分钟的学生,在创造力、抗挫折能力和跨学科思维3个维度上,得分高出同龄人47%。令人担忧的是,《2024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显示,未成年人日均纸质阅读时长28.06分钟,仍高于数字阅读;但对比2019年的数据,已下降12%。其他二三线城市和广大乡村地区,儿童的阅读时长应该跟上海呈现逐层减少的态势。
在深度阅读方面,社会正在失守。短视频、游戏等娱乐休闲,正在破坏儿童们应该着重训练的专注力和学习力。人不同于AI的地方,恰恰在于独立自主的、带批判性的灵性思维,以及人类拥有的情感共鸣。从古至今,人类文明始终需要能引导儿童深度阅读,并进化出专注力在内的一批批好书。
换句话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在AI时代,更要能够呵护灵性思维和情感共鸣的儿童阅读内核。余闲在《小云兜里的梦》中,用转学生龙小云和伤残教师俞婉芬的故事,试图引导读者特别是目标阅读群体——少年儿童们,去感受龙小云的学习成长心路历程,去共鸣俞婉芬老师挣扎振作的不屈精神。
龙小云决定克服结巴参加演讲比赛,就是想通过自主努力,结识镇长,为爸爸妈妈的养鸡场带来转机。她在小本子上写下的梦想,先是“考上大学”,然后“让俞老师振作”,再是“帮助爸爸”……一个敢想敢干的小女孩,慢慢地立了起来。读到小说的人,也累积了越来越多的共情,都希望她成功。这也佐证,《小云兜里的梦》达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AI时代新要求。
个人乡土经验与儿童生命教育的一例融合样本
在创作《小云兜里的梦》中,余闲曾请教乡村养猪和制作腊味的一些细节。尽管成书后,龙小云父母在浙江的创业项目变成了养鸡,但整部小说的乡土经验可以说有多处笔墨的着力。
第二章贵州老家的稻香鱼,第四章篾匠的手工竹艺和竹林鸡的生态养殖,第九章的矿难和山体滑坡,第十一章乡村的转型与振兴包括村里人创业做的文创、民宿、旅游,还有第十二章的新农人和新时代农业生产销售……这些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生活变迁细节,被描绘在故事里,为小说增色不少。
余闲曾在《三十六只蜂箱》的后记中写道,自己出生在乡村,对乡村原本就十分熟悉。工作后,他常去贵州支教。在《小云兜里的梦》里对贵州乡村生活和语言的描写,乃至对龙小云奶奶、父母的形象刻画,也就能信手拈来。
《小云兜里的梦》延续余闲将乡土经验与儿童生命教育融合的个人风格,开辟了一条鼓励和吸引少年儿童们观察生活、热爱生活和创造生活的希望大道。龙小云看到父母养的小鸡死掉时的伤心,听到小云兜村今非昔比的美丽蜕变故事的触动,参加演讲比赛勇敢克服困难的一路成长与创造,随着小说情节的演进,又一例儿童文学的融合样本得到呈现。
当然,生命教育还可以从人与自然,村子与生态,时代与乡村振兴等议题延展。龙小云在搜集演讲素材时,小说引出过去村子过度采矿、环境污染,到如今坚定转型建设美丽乡村的全过程。通过一个个村里的人物和叙事,从龙小云的视角,让少年儿童们在阅读体验中,站在更高维度,理解人、万物和生态的体系概念,“像山一样思考。”
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在场主义”
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细致入微,是《小云兜里的梦》的一大特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显示,相比城市青少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对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高、行为问题显著以及积极心理品质有待提升等方面。
可以说,余闲的这次儿童文学创作恰逢其时,他又是持证心理咨询师,在《小云兜里的梦》中,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小说不仅设计了小学教师俞婉芬救人致残后,从语文老师转岗为心理老师,还有大量的心理活动情节描写。如在插叙龙小云贵州老家村里生活时,从内心想象切入:“奶奶好着急,她就闭上眼睛说:‘太阳快出来!’果然来了几天阳光普照,天地间金光灿烂。在村里人收割的时候,她得意扬扬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只可惜没有人知道她的功劳。”
一个从西部山区乡村转学到东部发达美丽乡村的女孩子,因为口吃结巴,在班上自我介绍、参加演讲比赛时状况频出。余闲在龙小云的故事里,运用了大量心理描写。
这些小说内容,没有停留在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升华到如何面对自己的心结,并正视和克服它们。《小云兜里的梦》让人身临其境,仿佛就在现场。通过对儿童心理的洞察与捕捉,一次次的心理活动情节把故事推向高潮。
同时,在故事的发生中,制造了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在场主义”。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心理状况或问题时,家长、老师都不一定在第一现场。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缺失的某些时候,需要其他形式的补位与补充。一部儿童生命教育小说,在少年儿童阅读体验时,传递“在场”的价值,发挥健康和积极的心理教育作用,极具意义。
余闲对身残志坚的俞婉芬老师的心理刻画也不少。从伤残后的绝望,到康复的煎熬,再到返校转岗的复杂心情,最后在射箭比赛初赛和决赛里的挣扎与制胜,俞婉芬跃然纸上,那么真实,又在普通中通过心理活动高大起来。
她的父亲会做弓箭和自己从小会射箭,到最后在残运会射箭比赛夺冠的故事情节,可以说是《小云兜里的梦》给人的又一个惊喜。这不禁让人想起纪伯伦的散文诗《致孩子》,诗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被喻为弓与箭。译本很多,最后两句我最乐见的翻译是:“孩子们在射手的弓里‘弯曲’喜乐吧!爱这一路飞翔的箭,也爱这无比稳定的弓。”
其实,师生何尝不是另一种父母和儿女?俞婉芬和龙小云,彼此鼓励,相互滋养,最后都成功超越过去的自我,和小云兜村一起完成蜕变与新生。龙小云这根“箭”具有了基本的独立自主和勇敢创造,她的老师俞婉芬、她的父母都像一把把“弓”,也变得稳定优秀。
纪伯伦的《致孩子》想要表达的是:孩子是独立的,是与父母平等的个体,父母只能给予孩子爱,不能代替他们思想、灵魂的形成。余闲在写《小云兜里的梦》前,是否就以此为精神主旨,还是在小说创作中受到影响?我没问,读完全书也觉得不必问。毕竟,一次别致的儿童生命教育,已悄然完成。
(《小云兜里的梦》,余闲著,大象出版社,2024年10月)
作者简介
李燕,媒体工作者,成都市作协会员,著有《为人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