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帆
当代散文写作以其宏阔与渊深,渐呈海纳百川的瑰丽雄奇。而无数细流的奔赴,千脉百汇的不舍昼夜,是这景致的最终成因。邱海文以其矢志不渝的执着和热爱,秉持万涓成水的虔敬,贡献了自己的又一朵浪花。读其散文新著《时光碎影》,在娓娓道来的低吟浅唱中,时常被其文辞光影的惊涛所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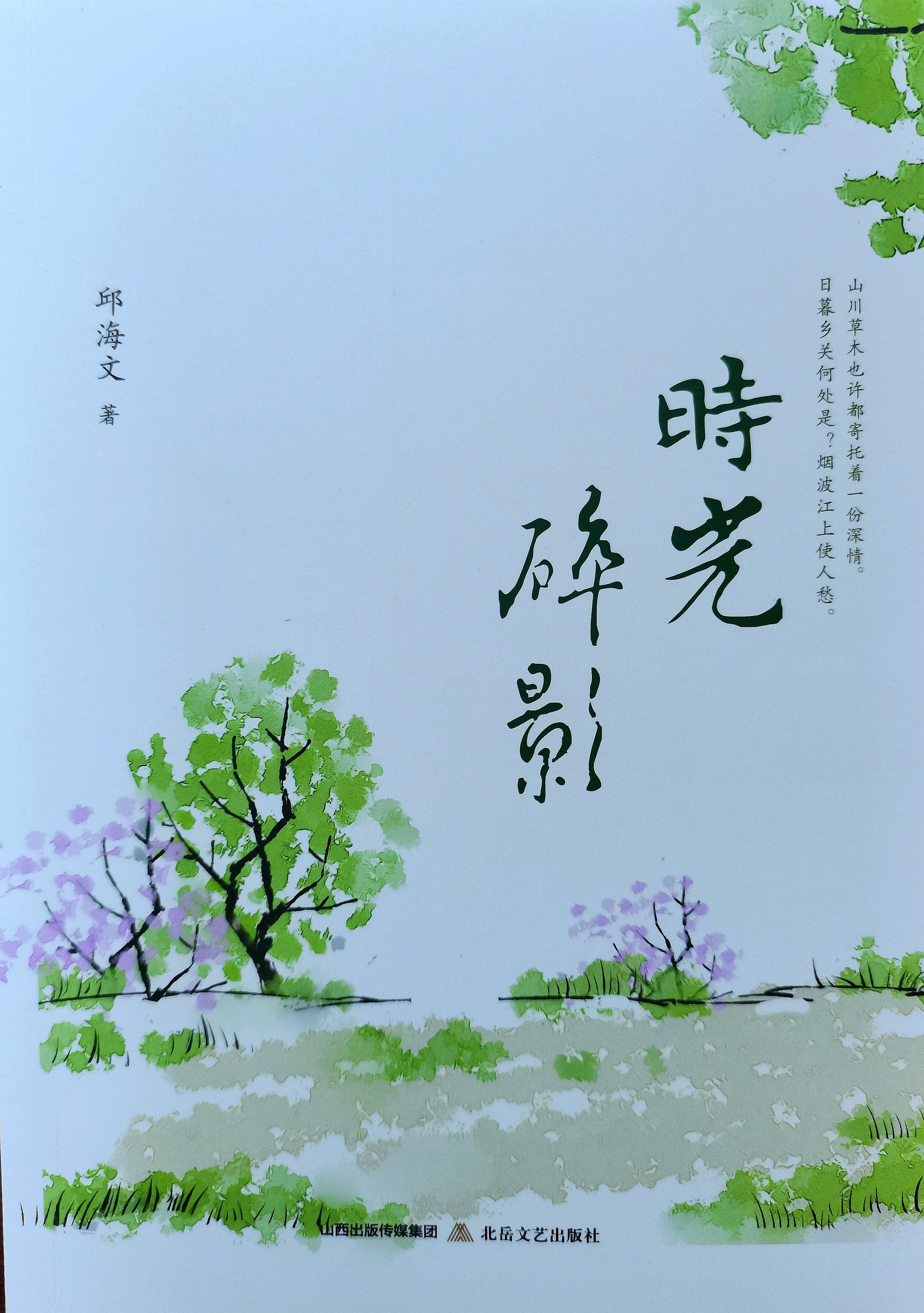
物象考量穿透史料价值。
阅历、经历、履历等经验含量的前置准备,是散文写作的门槛,也是登堂入室的必然“伴手礼”。
邱海文初出校园,便扎根于基层乡镇,重新打量并深悟大变革时代农业农村农民的命运转向。后来,他在多个部门的工作,为散文作家的底色,涂染了更浓墨重彩的一笔。
收在第一辑中的篇章,大多深沉悠远。作者善于从眼前物象起兴,使落墨获得张本,随即宕开一笔,在寻幽探古、钩沉考据般的条分缕析中,直追物象源头,让沉默在故纸、故土、故事中的往昔,在被打量回望的同时,重获鲜活耀眼的生机。
《何处寄乡关》具有寻根性质的开篇定调意味。在“湖广填四川”背景下展开的历史画卷,有对祖祖辈辈“来处”的追问,更有对自己扎根的一方水土的“此在”确证。他以轻风般的笔调,复现自己的古镇生活。“我住在古镇上,并在那里娶妻生子度过了十五个春秋。白天我用脚步丈量绵远河两岸的山水林田,夜晚则穿过逼仄昏暗的老街巷,枕着河水入眠……我曾配合省、市考古队对绵竹故城进行初探挖掘……可以说黄许镇留下了我的青春韶华,我对它的熟悉程度就如同面对自己的身体……”
正是基于这种如数家珍、深入骨髓的熟悉,那些闪烁于种种物象表面的光斑,才以深沉的历史感,折射出栖居的这片大地的乡愁可贵,也使看似平常的散文写作,具备厚重质地。
言象斟酌提炼文本价值。
散文毕竟是独辟蹊径的文体之一脉,在文史哲的打通包容之际,必然要求其特出的文本面貌,彰显其兼容之外的异质存在。
邱海文早年沉醉于诗歌写作,出版过诗集《开往春天的火车》。诗歌训练的有效性,首先体现在语言的精炼与准确。一个训练有素的诗者,必定是驾轻就熟的语言驭手。同时,文如其人。不同诗人的语言个性,又能有力消解文风的单一或趋同。
邱海文为人厚道持重又重情重义,为诗为文苦心孤诣又善于借鉴吸纳,这使他的语言既朴素沉稳又老练精到。他写景,既能工笔,也能写意。他怀人,既重描摹,又重剪影。他叙事,既擅密不透风,又擅疏可跑马。
“槎丫的梨花如飞雪曼舞,凋零的杨桃花残红点点,忙碌的蜜蜂翘尾扇翅,蛰在花蕊上。”点面之间,小大之间,动静之间,色泽之间,景与物之间,都有恰到好处的布白。一个“蛰”字的妙用,以聚焦之法,将细节之力和凝练之美,点缀得不露声色。
在《文学路上摆渡人》中,他深情回忆农民作家、良师益友谢星波:“爬格子是一件苦差事,不仅要耐得住寂寞,对文本反复琢磨、逐字推敲,还要实地走访,查阅大量资料,虽不至于‘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但都是精血之作。”他说自己“每次读书写字时不至于都要沐浴、更衣、焚香,那也是显得极其庄重肃穆,不敢对文字有丝毫亵渎和玩弄之意”。
在这个快进、快餐、快闪的时代,邱海文就这样以其近乎愚钝笨拙的“慢”,以其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硬功、耐力,精心打磨出他的散文集。语言是存在之乡,写作者对语言的敬重,是其葆有文本价值的可靠标识。
心象熔冶升华生命价值。
写作是我手写我心,是生命与灵魂的漫长对话。散文写作亦是如此。
文字和文学的命运,也是家国的命运。世道与人心、人性,必然在文字、文学中显影。哪怕沉默、隐忍,也会有基因般的火种,在亲情的燎原下复活。
邱海文在《跋》中说:“我本想写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描绘母性美丽的光辉,但一提起笔,种种生活点滴洪水般涌入眼帘,思绪万千,情不能抑,不知道该从何处落笔。也许只有时间才能抚平伤痛,才能从生活细微琐事中洗涤出钻石般的光彩。”
父母赐予我们生命,我们又以赤子般的忠贞,在横无际涯的历史长河上下求索,塑造文化文明的生命。然而有时候,这种“不能言,无法言”的难以言表,正是触及灵魂深处、深入生命内里,值得终生叩问和回答的使命所在。
海纳百川,文以载道。物象、言象、心象,终将汇流磅礴的汪洋。生命若一叶轻舟,载我们于宇宙洪荒或风平浪静处,细数那光影迷离的涵义与价值。
(《时光碎影》,邱海文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25年4月)
作者简介
张帆,四川省德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省音乐家协会、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出版专著《三星堆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