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明玉
长篇报告文学《羌山之门》,是陈霁继《雀儿山高度:其美多杰的故事》后的又一部纪实文学力作。该书通过作者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查阅、人物采访,历时两年创作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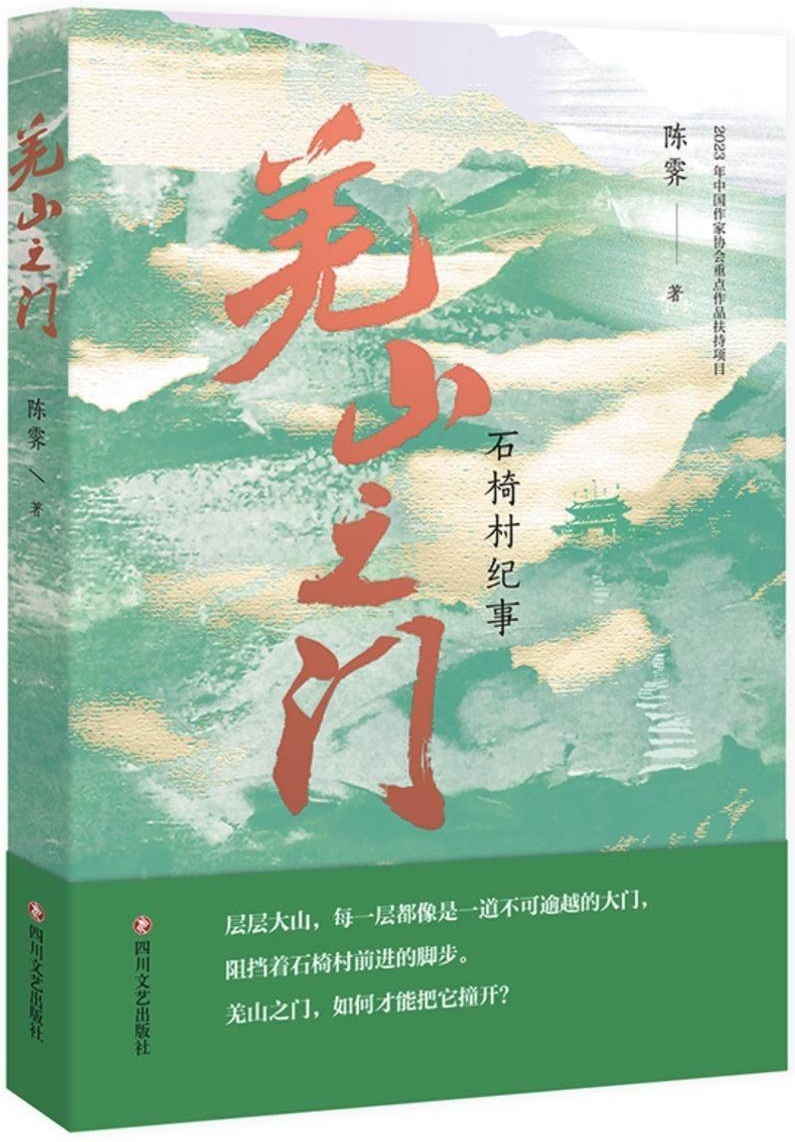
《羌山之门》以北川石椅村数十年来发生的历史巨变为描述对象,重点书写了自汶川特大地震以来,整个村庄是如何忍受生命与精神的创痛,在全国人民支持下进行灾后重建,又是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攻坚克难、振兴乡村的感人故事。
本书不仅还原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村民们通过坚忍不拔的品质、辛勤努力的奋进和聪明才智的有力施展,把“山中的家”变成“山水间的家”的历史真实,还展现出羌汉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水乳交融关系和不同凡响的民族团结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讲,《羌山之门》是一部兼容了人民奋斗历史、时代精神内涵与文学质地、艺术范式的纪实文学作品。
作为一部以纪实性为主的报告文学,理当是新闻真实与文学真实的高度融合。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高度融合,不单纯是创作观念、审美意识问题,更关系到作者采用怎样的叙事方式和艺术技巧。
仅从叙事方式的维度看,它既关涉到叙事的重点,也涉及叙事的节奏。就常态的叙事模式而论,一般是采用以写人为主、叙事为辅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将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重点,通过对人物情感、内心的细致描写,对人物行为、语言的艺术表达,对人物思想、灵魂的深层发掘,旨在凸显人物的独特蕴涵及其价值。
本书正是如此。首先采用的是平凡人叙事模式,将叙事的重点置于一群世世代代在山上刨食的村民身上,通过对这群人生活与生产、情感与内心历程的回叙,描写他们的日常琐碎和心中的理想,展现他们不平凡的精神品质,凸显他们创造的奇迹,从而达成由个人群像描摹到族群精神凸显、由家庭发展变迁映衬时代前进缩影的艺术表达。
聚焦石椅村历任村支书,极力展现其作为领头人的形象内涵和特殊意义,是这部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体现出的第一个特点。
首任村支书何国发,深度挖掘土地潜力,提高粮食单产,解决村民饿肚子的问题;陈明贵带领村民大面积种植茶叶,拓宽经济收入的渠道;刘耀德直击困扰石椅村的根本问题——道路不通,以舍我其谁的勇决、坚毅和担当,带领全体村民修筑“一条长两公里、宽三米的毛路”,开创石椅村人“要想富,先修路”的先河;陈财业把重点置于乡村社会发展的改革,积极开展产业结构调整。
在石椅村历任村支书中,邵再贵可谓是一位勇担大任的领头人。他先是致力于发展特色经济——在野生枇杷的基础上嫁接龙泉驿的优良枇杷,然后大搞农家乐经济,奠定后来石椅村产业的基本格局。
更为重要的是,邵再贵痛下决心,欲在悬崖绝壁上凿出一条公路,以打通山内与山外间的阻隔,彻底拔掉石椅村的“穷根”。这位悬崖上的“当代愚公”,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精神,克服了缺资金、缺技术、缺设备、缺后勤保障等重重困境,带领村民们一干就是3年,打通了险峻的大岩路,实现了汽车开进石椅村的当代奇观。
关注羌族文化名人,充分展示其在羌族文化传承、弘扬、创新过程中作出的贡献,是这部作品在人物形象方面体现出的第二个特点。
对置身大山深处的石椅村村民来说,“他们深知,没有文化的‘羌寨’只是一个空壳,必须借助活态的羌文化,复活一个真正的羌寨,石椅村的乡村旅游产业才能有生命力。”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村委会主任陈华全恳请母广元统领石椅羌寨的整个文化活动。这位统领人没有令人失望,他通过震撼的进寨仪式、敬酒仪式和夜间的篝火晚会,将原生态的山歌、口弦、羌笛、羌歌、羌舞、羌食、羌寨等民俗文化一一展现出来。
在石椅羌寨因股份制不成熟、股东经济实力不足和经营理念、抗压能力等诸多原因出现经营困难时,县民间艺术团团长、羌历年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华武主动接手过来,除尽力展示传统羌族文化元素外,还谋划在县城建一座博物馆,以陈列富于历史价值的羌族器物和唢呐、锣鼓、羌笛、口弦、羌绣等非遗物品,以令人们能够充分体验原生态的羌族生活。
如果说母广元、杨华武是羌族文化传承的引领者,那么,王安莲就是羌族文化符号的传授者。她不仅传授唱羌歌、跳羌舞、吹口弦等传统技艺,还让每一位石椅寨人,在日常劳作的间隙,或是忙完工作的夜晚,主动参与文化表演和文化传承,以此建构出一幅活态意义的羌族文化图景。
无论是对石椅村个体生命的深切关注,还是对其整个生命群体的深层聚焦,都无法绕开一个沉重的历史事件——汶川特大地震。这既是石椅村人共同经历的巨大灾难,也是其几代人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书写这场巨大灾难给石椅村带来的心灵创痛,便成为这部作品的重点内容之一。
为全景式地展现这场大地震给石椅村带来的深重灾难,作者几乎采访了所有的村民,获取了大量详实的资料和信息。在这个基点上,侧重选取了陈银业、陈建业、何国发及其家庭所遭受的重创,作为主要的叙事和描写对象。
那场灾难中的故事、场面、情节及细节,之所以能得以重现,是因为众多幸存者回忆和口述的结果,显示出口述价值和史料意义。
作者十分清楚,如果一味地描写那段痛彻心扉的往事,会在无形中增加人们内里的伤感和悲怆,也并非这部作品所要达到的目的。因而,他很快将笔锋一转,将叙事的重点置于石椅村人的现实存在和未来发展上。一方面极力描绘他们强忍着内心创痛,积极参与震后的家园重建,大力开展农业生产的恢复;另一方面用更为真实、铺陈的笔力,深度展现他们在未来发展历程中的努力与奋进精神。
其中,既有对乡村实施的重大改革举措,又有对产业结构富有力度的调整;既有对他地优良果树的主动引进,又有对乡村农家乐发展的升级改造;既有对羌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有羌族现代文明的开掘和创新。
作者的这番叙事和描写,不仅展现出石椅村人强大的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也揭示了当代中国乡村正在迈向更为广阔、更加幸福的思想意旨,从而充分展现出报告文学所具有的真实程度。
从文本学角度进行考察,这部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浓郁的四川韵味。
首先,以石椅村为聚焦对象,通过对人物与故事、事件与情节、场面与环境、社会与现实的描写,反映村子7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深层揭示造成这种巨大变化的根由,展现出独特的地方色彩。
其次,无论是对叙事、描写词汇的选取,还是对抒情、议论语言的采用,都掺入大量的四川方言或地方土语,表达出鲜明的四川特色。
综合上述特点而论,这部报告文学不仅是对四川山乡巨变历史的书写,也是对有着四川韵味文学样本的呈现。
(《羌山之门》,陈霁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5年5月)
作者简介
孔明玉,绵阳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