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非
我一直认为,人过40岁能写诗,或还能继续写诗,或许更能认清诗歌的本相,并可自觉获取艺术的密码。这样的写作,有别于青春期不可靠的灵感与思考乏力的自我激动。李文娟属于前者,以至于我得知她的第一本诗集《想让夜晚低一些》已出版时,不免心生诧异与好奇。
阅读这部诗集,我留意到李文娟下笔的独到之处,能以职业律师的理性洞察世情,又可以诗人的敏感触摸灵魂。“夜晚”作为她的精神世界的一种寄寓或容器,将古典诗词的意蕴、现代生活的痛感铸为诗性的晶体,以“低一些”的姿态完成对生命、爱与孤独的叩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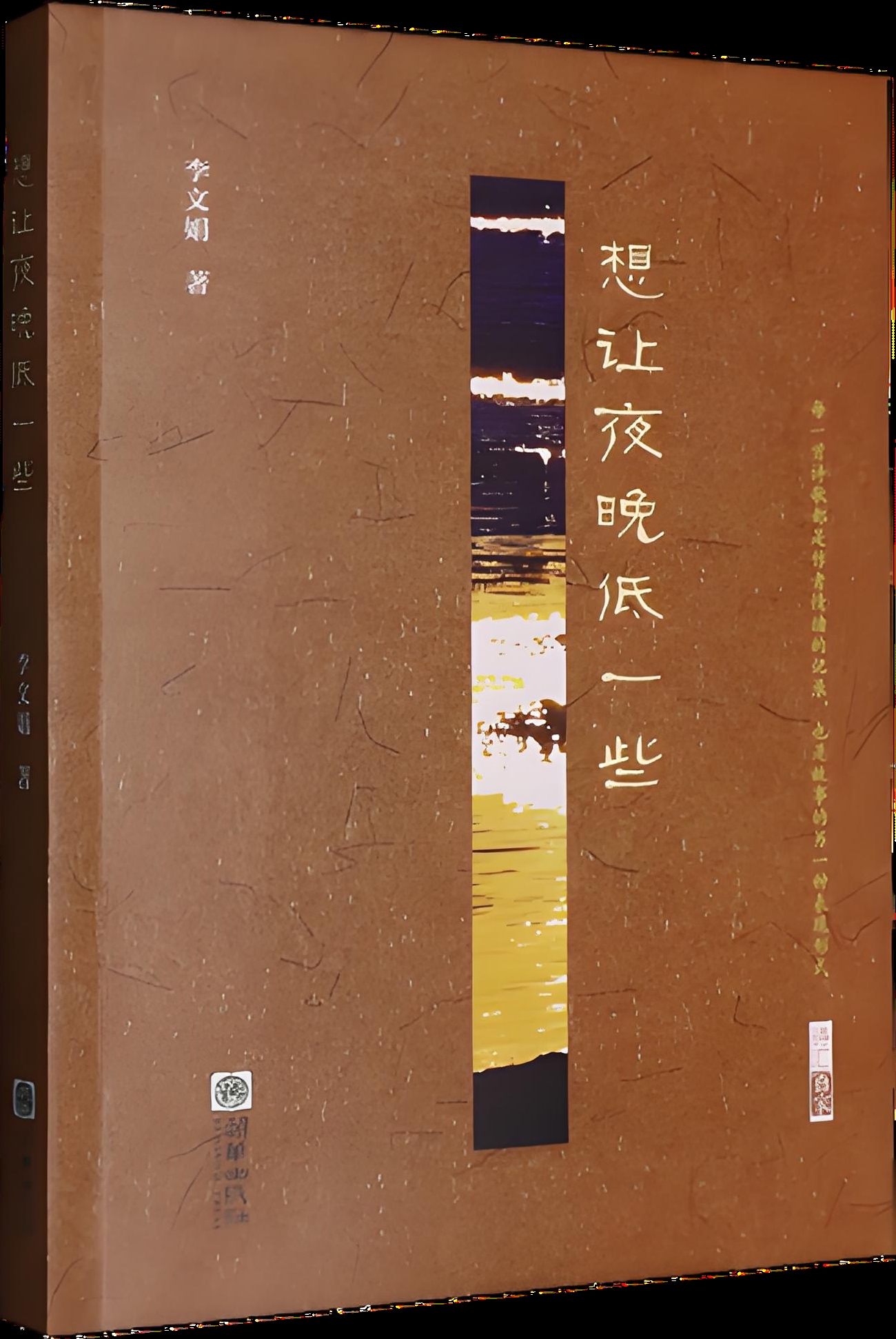
古典意象中的现代情殇
《想让夜晚低一些》是一部以爱情为主旨的诗集。开卷之诗《春山空》,诗人是这样起笔的:“那时树影只是梅花的烙印/水也只是一首词的背景/世界也没有那么复杂 想爱便爱”。寥寥数语,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转化为现代语境下的情感倾诉。“梅花”“水”“词”不再仅是意象与传统文人寄情的符号,而是成为诗人的情感碎片,打破了“月上柳梢头”的含蓄传统,直接道出她的心中所念:“我所在意的/不过是月下推门还是敲门”。
这样的表达,现代爱情的困惑,让古典意象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同时,在这首诗中,诗人对古典意象的重构性运用,还体现在时空折叠的技巧上:“有时西出阳关/有时烟花三月下扬州”, 将不同朝代的地理坐标并置,形成跨越时空的情感对话。这种通过“下雪的夜晚借着雪色/走一夜长路来到你门前/只为说一句早安”的现代行为,让古典的时空观在当代人的情感需求中获得新的叙事逻辑。
当“醉里挑灯回首半生戎马”与“次日一早就采菊东篱下”在同一诗中碰撞,历史的厚重与生活的轻盈形成张力,暗示着现代人在传统与现代中的精神突围。
序言《因为爱,隐隐作痛的并不都是伤口》指出,李文娟“在古典诗词的意蕴里不仅写出了现代人的情愫,而且写得如此洒脱、如此决绝”。在笔者看来,这种洒脱与决绝在《极甜的九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桂花被自己的狂热打翻在地/要经过一万次弯腰/才能捡起她们无意坠落的笑声”。
“桂花”这一古典意象在此被赋予狂欢化的现代性特质,“一万次弯腰”的夸张修辞,将传统诗词中“人闲桂花落”的静谧转化为充满肉身痛感的生命体验,让自然物象成为都市人情感挣扎的镜像。
在《写给那一去不复返的旧时光或故乡》诗中,诗人借梨花、春雨、小桥流水等古典意象,构建了极易产生共鸣的诗意空间。“春风得意马蹄疾”等古律的穿插引用,将古典诗词的音韵与老唱片、留声机等旧物并置,让泛黄的记忆在现代语境与现实生活中苏醒。“执手相看泪眼”的古典离别场景,与“飞行八万公里”的现代时空跨度形成张力,既见相思之深苦,亦暗喻都市人在漂泊中对精神原乡的永恒追寻。
继而,诗人又以泰山、乡音 为切入点,用“济南话里有故乡影子”的奇妙联想,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情感坐标。“从十三岁到四十岁/不过一首诗的时光”,以跳跃的蒙太奇手法浓缩半生漂泊的沧桑,而 “故乡在阳台上对坐/泡一壶稗子酒”的画面,将古典诗中“对影成三人” 转化为现代生活的日常瞬间。
这是意外的无奈——当故乡从“抱不住一缕炊烟”的衰老,变为可对坐放歌的知己时,暗藏着故土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没有体温符号化的怅惘。
黄昏也是古典意象群中的常客。《黄昏》一诗盛满现代情感的碎裂与惆怅。诗中月色、黄昏、秋水等传统意象,被赋予当代人情感的记忆——窗帘上的影子是昨夜的遗存,痛哭里陷落的不只是往事,更有被时间淘洗后的个体伤痕。“草长莺飞” 的江南春景以复沓句式铺陈,本是古典诗词中生机盎然的意象,在此成为梦境与现实的分割线。
鸽子“飞了九千里”坠入“远古”,暗喻个人情愫在时空错位中的无端迷失。20岁冬季望向秋水的凝视,与“头发真的白了”的沧桑喟叹,将古典的伤逝主题转化为现代生命体验的具象化表达,勾勒出对往事的追忆与时间流逝的感伤。铜镜、诺言与“地老天荒”的反讽,更以古典器物与现代誓言的碰撞,揭示出现代情殇在传统美学框架下的无情裂变。
疼痛与温柔的哲学思辨
在诗集的核心诗篇《想让夜晚低一些》中,诗人构建了一个充满悖论的爱的空间。开笔便直奔主题:“想让夜晚低一些/低过一些枣树和梨树/低过茅草和稻谷/低过山风 弯月/低过小孩的哭声和女人的眼泪”。
这里的“低”并非卑微的屈服,而是一种主动下沉的生命姿态,是为了“让一些事物安静下来”,包括“瘟疫 战火 欲望和悲伤/无休止的奋斗/没有终点的行走/还有在心上爬行的细碎的疼”。“女人的眼泪”与 “小孩的哭声”将抽象的爱,具象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更进一步,诗人还发现,“假如它低一些/就会看见花蕊/看见叶子粗粗的脉络/母亲手上的青筋/轻抚熟睡的儿童”,将悲悯与关怀暗置于多维空间,使诗歌获得诗学的张力。
李文娟的爱情书写,充满了疼痛与温柔的哲学思辨。在《删》一诗中, “脆弱到只需一根手指/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切断与昨天的全部联系/”,表面的云淡风轻暗藏着内心的挣扎,因为紧随其后是诗人的体悟:“多么深挚的幸福/多么铭心的伤痛”。
但这种疼痛并未导向绝望,而是在《不绝的路》中让自己的灵魂升腾:“即使冰雪让全世界凝固/即使爱已被悲伤冻成了化石/我们也要一起化为蝴蝶/从雪山上往下飞”。
这种态度是决绝的,自信力由此获得诗学的灌注。
值得关注的,是《叙事之一》《叙事之二》两首诗。前者以“悬崖边缘的行走”隐喻生存的悖论:当生活被赋予诗的滤镜,其“不真实感”恰是疼痛的根源——众人将光束聚焦于个体,期待“隐藏的堕落”,这种凝视本身构成无形的深渊。
这里的“温柔”蜷缩在词语的椎骨中:诗人以旁观者的“理解和怜悯”,承认疼痛的普遍性,又以看客的疏离揭示人类情感连接的局限。疼痛成为存在的证明,而温柔是对这一证明的无奈接纳,二者在“命”的框架下催生了艺术张力。
《叙事之二》一诗转向自然意象的哲学化书写:布谷鸟的“呜咽”将疼痛具象为季节的悲鸣,种植“紫藤、茅草、狗尾巴花”之举,以温柔的造物行为对抗孤独。庄稼地里的植物不再是单纯的景物,而是“给禾苗带来朋友”的存在主义实践:疼痛源于“孤独的禾苗”暗喻的生命的孤立,温柔是打破这种孤立的主动选择。诗中“种进”的动作暗含哲思:温柔不是被动的怜悯,而是通过创造解构疼痛的本质。在“看见”与“行动”的思辨中,完成对生存本质的哲学勘探。
这种对疼痛的凝视与温柔的主动创造,令人想到作品冷静又充满悖论的诺奖波兰诗人维斯拉瓦·辛波斯卡,她同样揭示人类存在的困境与局限,却总能在微小事物(如一颗沙粒、一次偶然)中,发现惊奇与悲悯。
李文娟诗中“承认疼痛的普遍性”与“通过种植紫藤茅草解构孤独”的实践,与辛波斯卡的精神向度遥相呼应——她们都清醒地认识到生命固有的底色,却都不放弃在具体的、微小的行动中(无论是写诗还是种花),寻找温柔作为对抗虚无、连接存在的桥梁。这种温柔,正如辛波斯卡所暗示的,不是廉价的安慰,而是直面荒诞后依然选择肯定生命细节的勇气。
情感暗夜的自我救赎
在《写给自己的明天》中,李文娟是自信的:“我的明天在仪式里烟雾缭绕/每个人都怀揣另一个自己”“由它来发动推翻陈旧往事的‘起义/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拿出拂尘”,完成对旧我的告别,让自我救赎的过程融入到真实的生活中,而不是唇齿间的呼号。
《在刀尖上舞蹈》以危险的平衡感隐喻生存的困境:“在刀尖上舞蹈/扔下花瓣的人 微微低垂的脸庞/就复活了树林”。这里的“刀尖”既是现实压力的象征,也是精神突围的支点,“扔下花瓣”的动作则暗示了痛苦中也能创造美的生命姿态。
诗人拒绝将自我救赎简化为廉价的乐观主义,而是如《慢性的疼》中所呈现的:“慢性的疼就是/不让你好好活着 也不让你死去/痛苦不屑于要人的命”,直面现代人生存的荒诞处境。这种清醒的痛感认知,让救赎书写避免落入空洞的心灵鸡汤式的说教。
李文娟在《当我意识到自己有灵魂》中完成的“俯瞰”与觉醒,其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心理描写。这不禁让人想到海德格尔关于“此在”本真状态的论述。
海德格尔认为,人常陷入日常的沉沦,而面对“畏”(尤其是对死亡的领悟),能促使人回到本真的自己,筹划自身的存在。李文娟诗中灵魂的“浮起”“俯瞰”“宽宥或拒绝”,正是这种从“沉沦”中挣脱,直面自身存在可能性的精神“越狱”。
她通过哲学家说的对生活的“诗意言说”进行的自我救赎与告别仪式,本质上是寻求“诗意地栖居”,在精神的暗夜中开辟一块可以守护本真、仰望星光的领地。通过这样的书写,诗人完成从身体觉醒到灵魂觉醒的升腾:“我的灵魂开始浮在五层楼顶/宽宥或者拒绝/排斥或接纳/俯瞰那些忙忙碌碌的肉身”。
自然物象的精神镜像
李文娟的诗歌中,自然物象不经然成了她的精神镜像。
在《空城》中,“一个人待久了/她身边的一切/都散发出寂寞的味道”,城市空间的冷漠通过“寂寞的味道”被感知,而“地图上一厘米”的距离丈量,暗示着现代人际关系的疏离。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乡下》:“一位背背篓的大妈/诉说去年一袋劣质种子带来的/一整年空空的盼望”。
乡村生活的艰辛被诗人包裹在“像抚摸自己的三个儿子”的温情比喻中,自然的丰饶与土地的厚重,成为治愈城市创伤的精神良药。
值得关注的是,诗人对自然的书写充满生命伦理的思考:“几天前还绿油油的衣裳/被强行扒到一边/藏匿了几个月的孩子/ 一个一个被掏空了”(《空空的地》),将土地的收获过程转化为充满痛感的身体叙事。“土地摸摸自己的肚皮/感到了空荡荡的满足”的拟人化描写,让自然获得主体意识。这种书写超越简单的环保主题,触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思考。
诗人的艺术触角已延伸至对生命、自然与故乡的广泛爱恋。在《我烟雨蒙蒙的祖国》一诗中,“祖国对于我/是一方滴水的屋檐/一只青瓷碗/一张床/和我亲爱的女儿”,将宏大的家国叙事消解为日常化的生命体验,让大情怀与小家庭实现融合。这种以小见大的书写策略,让烟雨蒙蒙的诗意氛围中渗透着泥土般的真实质感。
在《比枣花还小的喜悦》中,“母亲在田野里劳作的身影”与“山坡上多长了一棵枣树”的细节,将对故乡的眷恋转化为伸手可及的生活碎片,让爱的维度在微观叙事中获得诗意延展。
李文娟在跋文《秘密荒园》中写道:“这些诗歌,是我小小的秘密荒园。”这座荒园拒绝成为供人观赏的精致园林,而是保持“荒芜而又生机勃勃”的本真状态。正如她在诗中反复书写的“低一些”的生命姿态,表达了愿意在贴近大地的过程中感知生命的本真重量。
诗集《想让夜晚低一些》不仅是一部个人情感的结晶,更是一幅在当代精神荒原上寻求诗意栖居的心灵图谱。她以冷峻洞察现实之“刀尖”,以诗人的敏感在“低处”触摸灵魂的微光与自然的密语,像维斯拉瓦·辛波斯卡一样,不回避现代爱情与生存中的疼痛、悖论与荒诞,始终在古典意象的现代转生、在疼痛与温柔的思辨缠绕、在微小自然物象的观照中,实践着清醒的温柔。
当夜晚真的“低一些”时,我们窥见的,不仅是诗意之网兜住的泪水与梦境,更是在存在之暗夜中,一个灵魂如何通过低吟与升腾确认自身位置,并试图为世界“披一床温柔的毯子”的历程。
(《想让夜晚低一些》,李文娟著,朝华出版社,2025年2月)
作者简介
贾非,1988年始笔于军营,同年发表作品。西华师范大学MBA校外导师。诗作散见于《诗刊》《解放军文艺》《星星》《作品》《诗潮》《湖南文学》《西部》《中国青年报》《四川日报》等;诗评见《创作评谭》《杨子江文学评论》《星星·理论版》《诗潮》《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等。著有诗集《世纪铜号》《飞天的长城》等诗歌随笔、长篇小说4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