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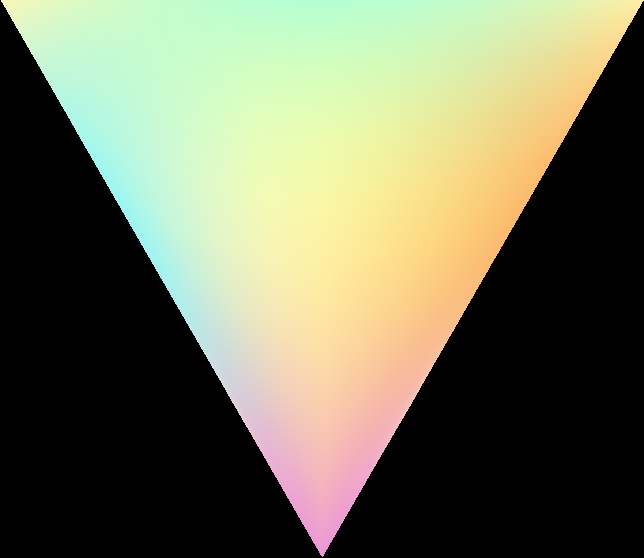
由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戏剧家协会指导,陈智林任艺术总监,张平导演的川剧《欧阳修》,6月27日和28日晚在成都首演。该剧以独特的回忆笔法,回溯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跌宕起伏又心怀天下的一生。川观新闻文化频道和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西岭雪”文艺评论版,特别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对该剧展开评论,以飨读者。
刘海琨
川剧《欧阳修》整体风格融合传统川剧的唱念做打与现代剧场美学,以恢弘叙事与诗意写意交织的方式,展开对北宋文学巨匠欧阳修一生的追溯。剧作采用倒叙结构,以暮年欧阳修与弟子苏轼、苏辙、曾巩共叙旧事为引,通过一系列闪回,串联起三度贬谪、力主新政、诲人不倦的生命篇章,塑造了一位可亲、可感、可敬的文坛宗师形象。
文气:风流未减是文章
欧阳修一生,文章盖世,风流自成气度。剧作从史料根基入手,结合生活化细节,勾勒出一个有风骨、有风趣、有风情的才子典型。
开篇设定于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奉诏承担《新唐书》本纪、志、表的编撰与全书统稿重任。面对苏轼、苏辙、曾巩3个门生,他出一题考问:“一匹飞马踩死一条狗,应当如何书写?”苏轼云:“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苏辙曰:“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曾巩亦拟长句。欧阳修却只写5字:“逸马杀犬于道。”简洁精准,体现出文贵简练的史家之道。
这种才情之韵,贯穿于剧中的生活化描写。在第二场“花灯会”中,剧作虚构欧阳修与发妻薛氏邂逅的浪漫段落,颇具《西厢记》式的文人风情。
上元佳节,灯火辉映,游人如织。欧阳修随友赏灯,偶遇才情出众的女子——户部侍郎之女薛四小姐。薛小姐巧设灯谜,欧阳修对答如流。听其作答,薛小姐不禁脱口赞叹:“此君虽无潘安貌,句句珠玑出九皋。文气焕彩星光耀,诗入芳心起春潮。”丫环因其家世寒微欲阻之,幸得梅尧臣从中撮合,道出“此人便是作《浪淘沙·把酒祝东风》者”。这一段戏结构紧凑,语词隽永,通过语言的精致铺陈与人物关系的层层递进,将一场文人邂逅演绎得生活化而不流俗,风雅而不做作。
整个剧作中的欧阳修,既是史官、词人,更是风骨与风情并重的士人。他既能在朝堂上以犀利笔锋批时弊,又能在花灯夜市中巧对香闺芳华;既有“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担当,也不失“举杯邀月”之浪漫。川剧《欧阳修》以舞台的方式,勾勒出一个文人的理想人格形象。如此塑像,使欧阳修不再是史书中的符号,而成为观众眼中可亲、可信、可感的文化人格的化身。
文胆:万言奏疏敢直言
除了才情,《欧阳修》更着力刻画其“文人之胆”。
在“庆历新政”一幕,欧阳修作为改革核心人物之一,力主“明黜陟、抑侥幸”,大刀阔斧改革官制。唱词中更借欧阳修之口指出:“若不革此弊,官皆私门之党,国何以治?”这一政治主张,直指官场痼疾,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尤其激起了保守派与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弹。
这场戏以“满堂对列”的编排,展现改革与守旧势力的正面交锋,背景墙悬挂仿宋代木格照壁,象征体制秩序之重。灯光从上而下投射,形如天命裁决,强化“孤忠之辩”的氛围。欧阳修唱腔刚劲,力陈利害,而守旧派以“朋党”之名加以攻击。高潮处,众臣交头接耳、面露冷笑,形成压迫感十足的氛围。这一幕不仅塑造了欧阳修“敢言之胆”,更书写他守正不阿的人格风骨。
尽管欧阳修竭力辩护,甚至撰《朋党论》澄清视听,仍难挽败局。新政遭废,他被贬滁州。在“夜行赴贬”这一幕中,舞台为冷蓝色调,背幕现远山、孤月、水影、荻花剪影。酒坛掩映于丛荻之间,形成“醉”与“寒”的双重意象。
欧阳修低唱四忧:“忧小人邀新宠,忧新政被断送,忧君子皆罢黜,忧江山缺金瓯。”这一唱段低缓深沉,唱尽一位文人对家国命运的无力与不舍。惆怅之际,欧阳修母亲登场,引发回忆:幼年父亡,家贫至极,折荻为笔,沙地为纸,从“画荻教子”中习得笔耕不辍的初心。
这一荻花意象,在舞台上形成全剧象征性母题——其一笔写尽峥嵘岁月,也承载清贫家教与精神赓续。
在母亲劝导下,欧阳修重拾初心,振作精神,于滁州推行地方新政,劝课农桑,兴办义学,施行宽简之政,使一方百姓得安养。唱词中云:“水入渊泽蓄势久,他日也做浩浩流。”
文人之胆,并非一味硬刚之勇,而是知进退、明权衡的从容与沉毅。欧阳修在落魄时不自怨自艾,而是守住内心的光亮,于困顿中积蓄力量,于沉潜中等待时机。那种不以成败论英雄、不因贬谪改志向的千钧之力,恰是“文人之胆”的最高境界。
文脉:传道授业有人继
一位真正的文人,其意义不止于一时之政,而在其文脉传承。欧阳修之“文”,不仅是文章风骨,更是一种为学、为人、为政的整体境界。他之所以被尊为“一代文宗”,不在于名篇若干,而在于培养出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等北宋文坛中坚,开创“唐宋八大家”之一脉。剧中对此传承有两段重点书写。
一为滁州山林之乐。新政小试得效后,欧阳修邀晏殊、范仲淹、梅尧臣等共游琅琊,春山如洗,泉声潺潺。舞台以远山蓝绿设色,亭台、垂枝、光影交错,构成一幅春游图卷。酒酣之际,他提笔写下《醉翁亭记》,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唤起文风转向自然、体察民情的新文风,一时洛阳纸贵。
二为贡院科举审卷之争。嘉祐年间,欧阳修任主考官。他深知“文风即仕风”,文风不正,则仕途功业皆失其本。他洞察当时科场中“太学体”之弊,诸生文辞堆砌、空洞华靡,脱离现实,不通政理。为拨乱反正,他在考试中大胆黜落浮靡文风,排除条子推荐,唯才是举,最终拔擢苏轼等后起之秀。
剧中一段贡院门外的群众戏颇具张力,太学生围堵状元榜,怒指欧阳修“以朋党挟私”,欧阳修临场自辩,指出文章之弊:“文词艰涩、食古不化、脱离现实。”他对太学生既有严责,更怀关切:“文章为天下而作,不可为名而作。愿君等明年再试,当鸣惊人。”舞台于此化严为温,演绎出“文章关乎国是,教育关乎风骨”的士人风范。欧阳修之传道授业,不仅传文章技法,更传士人气节与为官之道。
在他与苏轼的交往中,师生情更近似忘年知己。剧中多次展现苏轼对老师的理解与尊敬,也展现欧阳修对弟子命运的关切。在新政失败后,他劝苏轼“刚强易折”,须“作壁上观”,显然是将半生跌宕沉浮化为经验传授。庄子曰:“安时而处顺。”欧阳修以自身颠沛起落,塑造了处世旷达、心怀苍生的文人之范。
结语
川剧《欧阳修》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人物传记剧,而是一部将文人精神通过舞台艺术加以复写与再造的作品。它以荻笔为喻,以文气为骨,以文胆为魂,以文脉为延,勾勒出一个既有铁骨担当,又不失风流雅致;既能济世经邦,又甘教书育人的古代士人形象。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欧阳修的壮阔人生,不只写在纸上,更立于人心。
作者简介
刘海琨,四川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评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2025年度四川文艺评论中心“有腔有调”川剧青年评论人才孵化项目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