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不群
“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这一次不是在埃特加·凯雷特的小说里,而是在谷禾新诗集《泥沼之子》开篇《世界的入口》中。广袤的宇宙中,带来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叩响世界的大门,“世界的入口,缓缓开启”,他以此返归并向世人宣告:“有什么,能阻挡我再一次诞生?”
为什么是“再一次”?因为这是朝着世界回归的“泥沼之子”,他早已经历过人间千般绚烂万般哀愁,双脚还浸在爱与痛的水深火热中,却从“泥沼”向着“无限”升起,在“世界的入口”敲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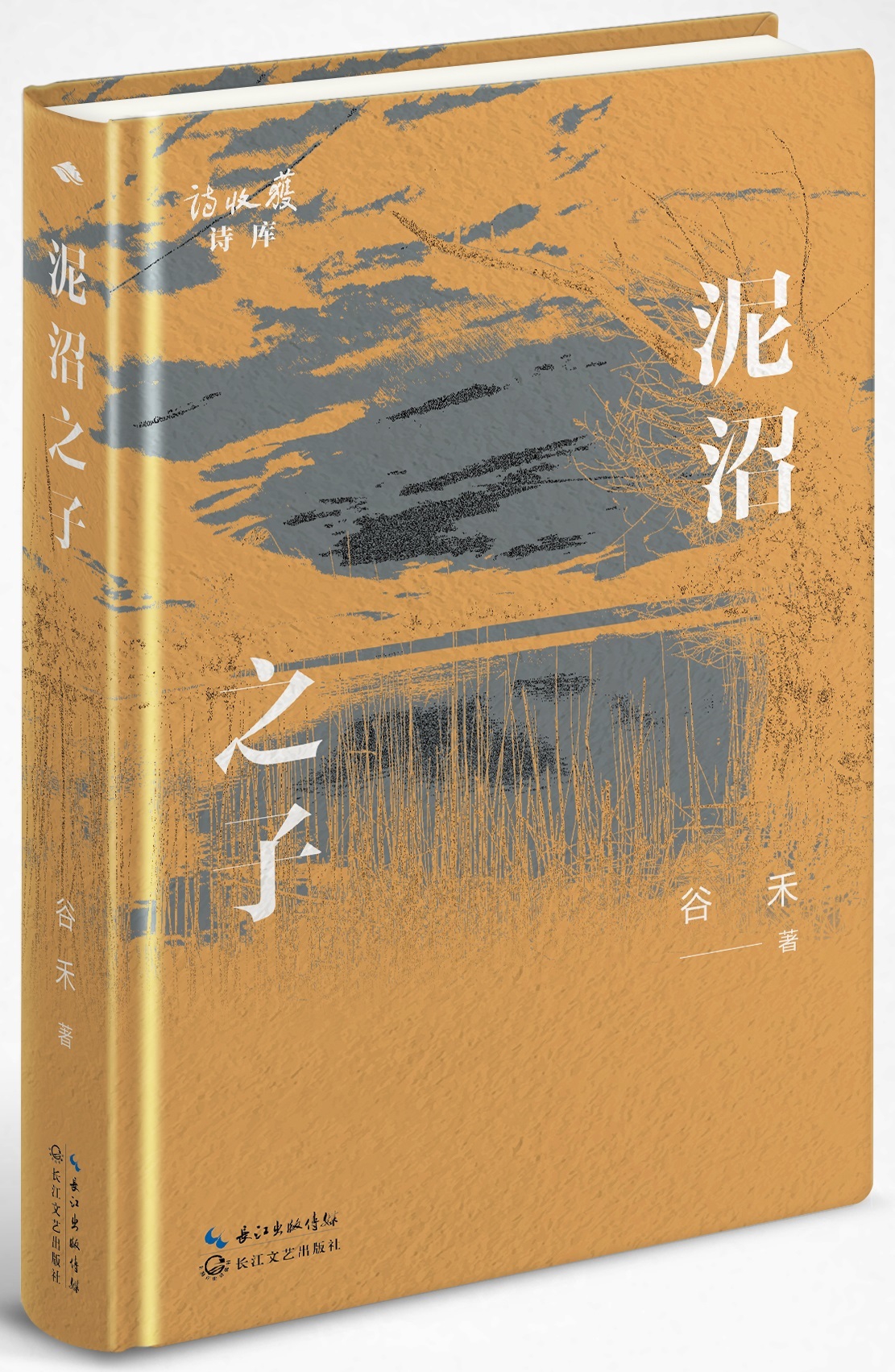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的隐喻说尽生命的热烈与荒芜。作为农家之子,谷禾出生在华夏文化蒸晒的核心地带,不得不赤脚从麦芒上踏过,用脚心的敏感感受文化血缘的奔涌与生命刺痛的呼喊,二者撞击燃起的大火时刻灼烧着他的胸口。“谁的头颅在泥沼中滚动?”(《把荒野抬高》)
这个想要化身泥丸、混同于尘埃的“头颅”,看见往日的同事“把生命交给了一瓶甲胺磷”,像“一块石子,奋力/掷向天心深处”(《一张旧照片》);看见“生活在乡下的父母,衰老/一点点损耗他们,把他们变成/汪着雨的枯枝”(《低语》);看见老人与小孩“抱紧一棵树,又笑又哭”(《树林记》);看见大雨之夜“推开门,走进大雨里”的父亲们“被更多车灯的远光照见,浮现又消失……”(《大雨之夜》)。
对亲人的回忆、对往事的怀想、对个体的关注,在我的眼前慢慢浮现出一个高挑、瘦削、脸庞微侧的诗人的雕像来。我与谷禾虽只有一二面之缘,却感觉到他的憨厚、朴实,不善言辞。他像一匹马,“沉默、倔强,人群中无际的孤单”(《马说》)。也许更愿生活在世界的内部,在一盏灯的相伴下,把内心的滚烫化为一个个文字的奔跑。
当他从中原走来,穿越历史的廊道,抚摸、拍打那些龙钟的古柏,听它们从虬曲的绿云中讲出千百年亘古不变的故事,他看见“利禄功名皆散尽,山水还回旧容颜/被搬动的石头,以青苔作袈裟/暮鼓撞击岩壁,胸腔里迸溅出狼嚎/与狮吼……乱雪扑向群峰/古柏支撑的庙宇,顷刻化作齑粉”(《古柏赋》)。历史与现实如鬼怪般捉摸不定,而生活中的苦难,如梵高所说,永远没有尽头。
那么,面对“……生活的、透明杯子,你要端起哪一个?/苦咖啡咽在喉咙里,一个声音在说:/“我偏爱它的难以下咽……”(《低语》)。生活之苦必然要穿过喉咙,找到善于发酵的肺腑,找到属于它的心田,在密闭空间中实施对生活之苦的克服,实现审美的绽放。
美国诗人简•赫斯菲尔德在《十扇窗》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当世界上的苦难和美被带入艺术中,它就变成了一个能重新塑造与重新校准人类与我们生活的形态、事件和理解的机会。”
而处在沉默中的诗人独自承受着苦难与美的双重冲撞,思量的正是生活的本义,就像那神秘的月亮:“月亮哦,她的神秘主义也仅是一层外衣/亿万斯年,她从不曾衰老/只在为你抵挡天外灾异的撞击中,早已遍体鳞伤”(《孤月高悬》)。诗人就是那枚月亮,他“早已遍体鳞伤”,但对于生活,他仍“偏爱它的难以下咽”,他着意摄取、提纯,把它养在喉咙里,喂养它,使它在那里慢慢蓄积、孵化、长大,成为一个爆破音,从“深喉里发出近于人的唳叫”。
天心月圆时,
仿佛纸上来客——
我怀疑它以飞之名
掏空了自己
——《跟从一只白鹭》
从生活的深重之苦中起飞的这一只鸟儿,从泥沼之中脱尽泥水、振翅飞鸣的这一只鸟儿,在纸上飞越心灵的千山万水,带着一颗纯粹之心落下,它“掏空了自己”,但又“并不耗损其作为鹭鸟的完整性”。它叫得越多,它身体里的歌谣就会生成得更多。正是这一只鸟儿,在千山飞尽后,明白了“……众山之上,不再有/更高的存在/唯星空,白云,空虚,和厌倦/一种伟大的荒凉”(《绝顶论》)。
他写下的人世,都闪现黑洞般的深渊。他写下的星空,都带着人间的温热,化作一片旷野。当他写下世界,仍然是从宇宙深处观看。
这里需要提到谷禾近年来集中精力撰写的探索性作品《无限》,它集诗歌、集章、札记、箴言等于一体,共126章,其中72章作为第二辑,收入本书。
在小序中,诗人开宗明义:“《无限》多为残片,如同一个人时常中断的纷乱思维,它重于记录、见证、个人思考和冥想,除个人日常生活和阅读的随记,形式上借鉴了集章、随笔、时文篡改、拼贴、微小说等文体。《无限》是无序而杂乱的,但在我心中,这种无序和杂乱才更接近‘诗’的原生态……”
以泥沙俱下的气势造成文本风格的粗砺,象征着心灵的自由和天然,带上原始文献和历史记录的气息。但它仍是诗人对诗与思的个人探索录。跟随着诗人的脚步,我们发现它是诗人勘破人世与宇宙之谜后对生命与宇宙重构,其根本在于“虚无”二字。
《无限》的第一章转述了宇宙循环理论,追溯到生命的始初,即宇宙大爆炸。最后一章却有短短9个字:“诗从虚无处,汹涌而来……”从开头到结尾形成一个闭环,以诗歌循环对应宇宙循环,在始与末的中间,是无数心灵碎片,是宇宙信息的交换、碰撞,新的诗歌与粒子的生成,新宇宙的再一次爆炸。
面向虚无的写作,使诗人主体获得解放与自由,从泥沼中抽拔而出,甚至从生与死中抽拔而出,获得完全的敞开。
阅读这部诗集,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转向,从万有到空无,从热烈到平息,从实体到虚无。谷禾的眼睛不再只盯着那些陷在泥沼中的人,不再只为生命中的爱与痛歌唱,而将视野投向更广大的视域,向着宇宙的始初超越,从生命之渺小与宇宙洪荒的对比带来的震撼,进入生命循环的感发,看见虚无之生生不息。
在BBC出品的纪录片《万物与虚无》里,物理学家吉姆•艾尔-哈利利探讨了万物与虚无的本质,指出万物本质上是虚无中一次量子波动的残余,从虚无中诞生宇宙终将归于虚无。虚无才是宇宙中的生生之母,万源之源。
从这样的眼里,看见的是“万物轰鸣,向上生枝开花,/愈来愈接近殡仪馆入云的烟囱”(《春风起》),是“……唯一城灯火/交织着光芒,更多蟋蟀的叫声,/从灯火深处隐隐传来”(《无限》第11章)。这生与死的相交相缠,辉煌与荒凉的相生相发,既是生生之境,又是枯萎之地,超越了人间对生与死的界定。
如此情境,让诗人仿佛独自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独坐雨外,听雨打山河,无始,又无终。”(《八月》)正是这“无始,又无终”的“雨打山河”,让诗人仿佛置身于事外,生与死都不再与他有关。他关注的只是星群的运行,空间的明灭,是大尺度观照下的平静与淡漠。
由此,我们也才明了“那些永恒的事物都在消逝”的涵义,永恒与消逝的龃龉、抵牾在此被消弭,万物消逝又不断涌现,在这消逝与涌现的无限循环中实现永恒。
华莱士•史蒂文斯在1942年创作的长诗《朝向最高虚构的笔记》第三部分“它必须带来快乐”中反复吟唱:“那虚无便是一种赤裸,是一个临界点。”此处的“赤裸”既指身体的赤裸,也指主体处于一个毫无遮蔽的状态,完全敞开,从“一个临界点”上朝向生与死的两端,这就是说它是一只“双头鹰”,一面朝向生,一面朝向死。
处于该“临界点”上的诗人,“仿佛成了自己所看到的那飞升的翅膀,/凭借它们在轨道的外层星球间移动,/降落到孩子们所躺的床上。”这“孩子”让我们想起《世界的入口》中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死亡为新生接生。
在《无限》第49章,谷禾引用苏珊•桑塔格的一句话:“疾病是生命的阴面。”并阐发说:“但对于我来说,疾病既非隐喻,亦非天道,而是另一个故乡——它终生寄宿在我的身体里”。
苏珊•桑塔格所谓生命的阴面的说法,应是来源于里尔克。1923年初,刚从巅峰状态中完成《致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杜伊诺哀歌》两部传世之作后不久,里尔克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像月球一样,生命肯定也有始终背向我们的一面,但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对生命的补充,使之至臻完美,变成全数,变成真实、福乐和圆全的存在之域与存在之球。”
1925年,在回答维托尔德•于勒维的问卷时,他又进一步阐述:“肯定生与肯定死在《哀歌》(指《杜伊诺哀歌》——引者注)中被证明为一件事……死是生的另一面,它背向我们,我们不曾与它照面:我们的此在(Dasein)以两个没有界限的领域为家,从二者中取得无穷的滋养,我们必须尝试对它取得最大的意识……真实的生命形态穿越两个界域,最宏大的循环之血涌过二者:既无此岸也无彼岸,唯有宏大的统一。”
在这里,里尔克表达的与史蒂文斯的“临界点”以及谷禾所说“疾病既非隐喻,亦非天道,而是另一个故乡——它终生寄宿在我的身体里”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跳出人之生存的视角,用更大的共同体,将生与死统合在一起,从一个更全面的视野理解生命,理解存在,而虚无正是生命的归宿,又是生命的出发点。
在虚无的巨大洞穴里,生命不断返归,又不断出发,无休无止如宇宙的循环生成与寂灭。所以,我们会发现谷禾常常调转思路,生命之路不是从生到死,而是从死到生:“我父亲用了一辈子的桌子/一直想回去森林里/成为继续生长的大树”(《无限》第71章),“许多年后/一滴水/从大海出发/溯流而上/涌上群峰之巅/让一棵枯树/抽出新芽”(《无限》第82章)。生命的“逆流而动”,显示出它超越世俗,超越人性的一面,是大宇宙中无穷的循环,就像“奥斯威辛。废弃的焚尸炉。一只蝴蝶/从落日的火焰中飞出——”(《无限》第29章)。
这只从“焚尸炉”中飞出的“蝴蝶”脱尽炮火与恐惧,也脱尽愤怒与仇恨,以其轻盈和灵动,超越死的沉重,带领所有生命的灰烬振翅高飞,并用翅膀扇起的风暴旋动粒子流,穿越星系和黑洞。
华莱士•史蒂文斯在《圣阿默勒教堂外观》一诗中曾写道:“在它灰烬般的否定中,有一个肯定的余烬。”这只蝴蝶所带领的飞翔的灰烬所完成的,正是将世界从否定转向肯定,把落日重新推向山巅,由此,“世界‘咔嚓’一声,得以重启。”(《一个生态摄影师的清晨》)
(《泥沼之子》,谷禾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