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劲廷
杨献平诗集《万物照心》,一改其惯常的散文创作风格,从幽微入手,窥看人性景象,深剜现代人存在的隐匿性症候。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献平更像是一个“拾荒者”,关注着那些近乎被大众废弃的遗存,以期找到拯救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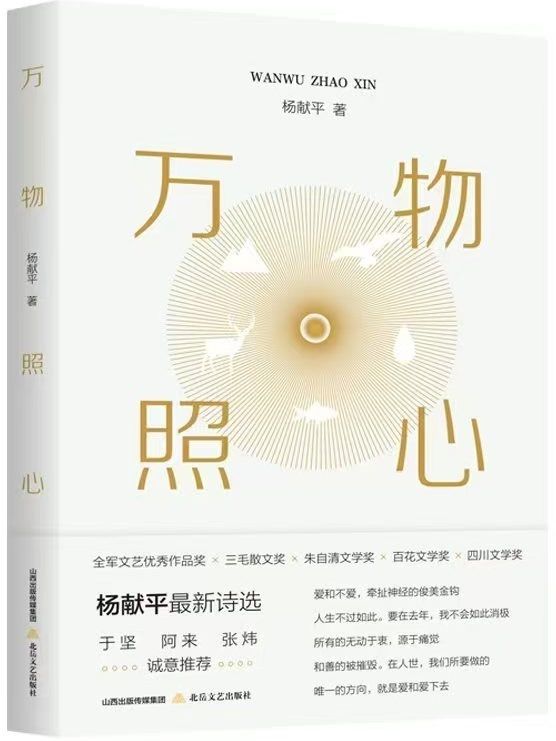
“拾荒”路径
杨献平的“拾荒”实践出自庸常生活中的琐碎与点滴,由此生发出与外部世界的情感共鸣。诗人并不敢笃定那些生活中的零碎是否可以表征他者的精神指归,所以并未直陈自身经验价值,也不愿灌输自身的意识认知。他旨在收纳流落在生命中的情感碎片,并将之整合成为诗性语言,由此建立一条自幽微而窥宏大的表达路径。
他从一杯不太引人注目的咖啡中,生成了现代人习惯性的冥思:“倘若有暗语从窗外抵达/谁将收下内心的狂奔”(《在莫舍咖啡》),也从一段被废弃遗忘的铁轨上感知到生命的流转与逝去:“人生总是需要刹那间忘我/就像你无意中递过来的体温/还有一些香气/从鼻翼绕道内心”(《废铁轨上的一个下午》)。撩拨诗人鼻息的不是这些细小颗粒本身,而是在殊异的人生尺度里,找寻自身经验与外界认知的契合,开掘人类本真的生存方式或生活状态。
恰似包括乔纳森•卡勒在内的现代论者一样,他们并不关心文学的本质或定义,而是将之视为“杂草”。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作为“拾荒者”的诗人,其重心不在于那些碎片化的“杂草”本身,而在于更宏伟的目标——表征荒废的“杂草”被人为定义的过程。
杨献平的实践不是在众声喧哗的当下作园丁式的“除杂”,而是在灵魂与气质匮乏的荒园中探秘“杂草”与“拾荒”诗人共通的生命旅程,并自觉地将这一探秘凝练文学使命。如书名《万物照心》一样,他直面被摒弃在大众视野外的卑微万物,聆听饱含生命意识的细碎清音,借机安放早已“趔趄的灵魂”与“踉跄的脚步”。
“拾荒”对象
杨献平的诗歌表达不只是对生活遗存的同情与忧悯,而是对生命引申意义的继续阐释,通过对欲望的满足,实现现代人精神面貌的还原,从而形成与“拾荒”行为有着共同价值取向的思想基底。
杨献平以冷峻平实的言语关切芸芸众生,静心造访他们的生存策略——心境、感悟、文化与人生,一如他关切着人体精神内部的空心化,甘愿将泪水滴落在每一寸驻留过的土壤,并将之作为播撒颂赞与敬意的地方。
“春日繁华/阳光可能摸到你的嘴唇/或许你已经是白骨一堆/仍保持生前的卑微”(《清明祭奠父亲》)。对逝去生命的无奈,对当下的难以把握与维系,诗人站在前人倒下的旧土堆上表达着无奈,却又只能以谎言欺瞒自己,借机腾出内省的心灵空间。
“现在他们都走了/我翻遍世上的柴灰/也没找到一粒火”(《那时候》)。诗人有意替那些尚未彻底枯萎的生命掸去蒙尘,从其生命的余晖中攫取一个不再容易被遗忘的真诚定义。以皲裂的手掌触摸大地的裂纹,以佝偻的身子裹紧众生,以枯萎的面容贴近同样枯萎的情感。
“拾荒”目的
缭乱的思绪和杂糅的情结反复跳跃在诗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夹缝中,一股无处不在的内在体验力,驱使着他铭记故乡的辽远、当下的浑噩与自我的颓唐。“如果能够瞬间老去/世界/我会用灵魂向你示好/并且用皱纹/给你最贴切的呼喊与拥抱”(《一个人的下午》)。“人生至此/我们爱的越来越少/慈悲却成倍增长”(《春节》)。故乡是否保持其恒定的原义?故人是否还是曾经谙熟的模样?从行为面向上看,作为拾荒者的杨献平,其诗歌创作旨趣在于不打扰灵魂,却又令人接近灵魂。
诗歌作为诗人对生活的戏仿,因其言语天然的隐蔽性而难以被大众觉察,却总在以不可名状的方式发出感召力。于杨献平而言,那些碎片不过是编织完整生命的断章,因而将之改译为精致优雅的诗性语言。他在一座诡异却摇曳生姿的百宝园中,发掘与资取“荒废”的原初价值或衍生价值,拆解被人持续书写的谜面,最终求得解脱与释怀,方得以在精神荒原上完成一场拾荒者的自我拯救。
(《万物照心》,杨献平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