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海龙
李劲峰的散文集《且听风吟》,编排是精心设计的:第一辑“援藏记事”(8篇),第二辑“生活随笔”(33篇),第三辑“女儿成长记录”(21篇)。
江河奔流,大地如诗。《且听风吟》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而是从生活的细节中,自然而然地流出心境,演绎着市井烟火的别样旋律。从对自身命运的观照,映射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居闹市,始终怀念故乡;衣食足,永远忘不了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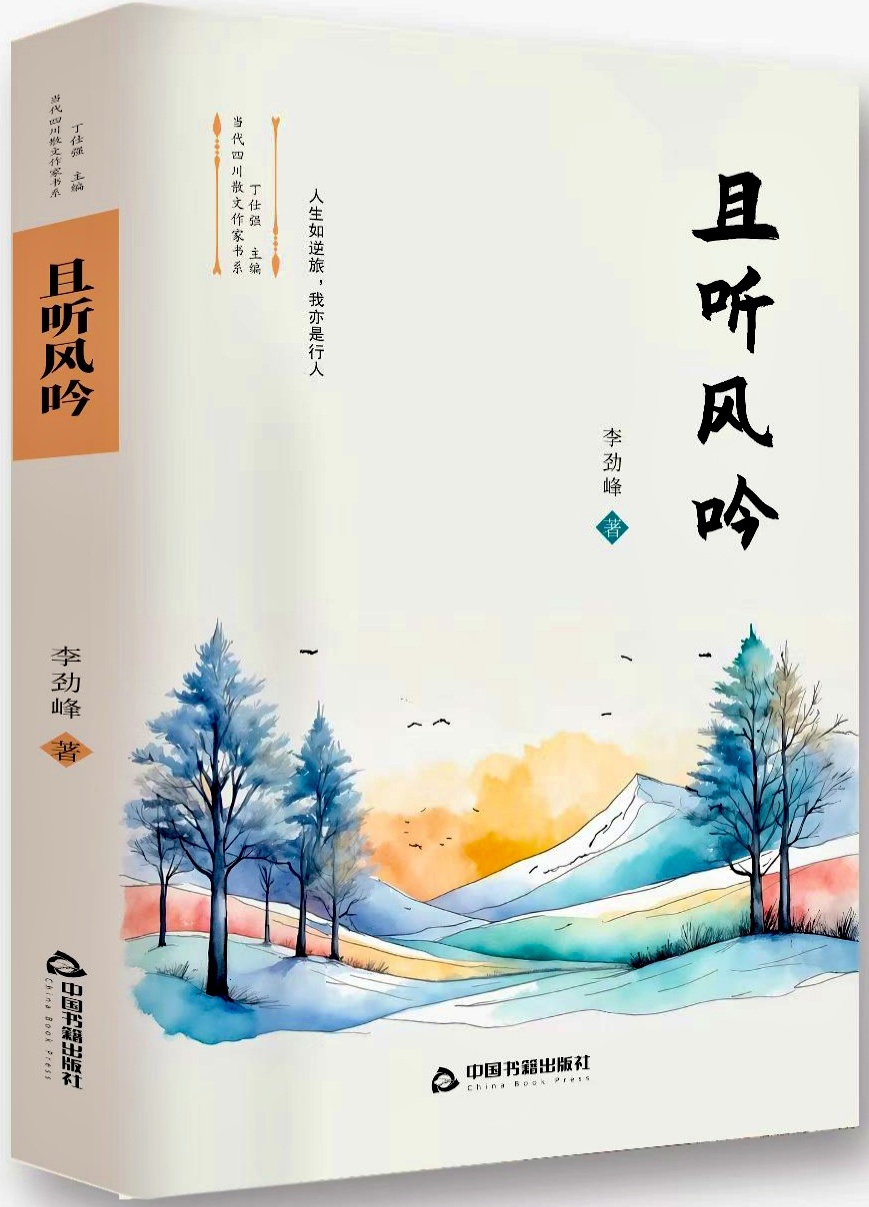
“且听风吟”4字,已昭示了作者对抗时代噪音的文学立场。在众声喧哗中,侧耳聆听风的低语,聆听土地的心跳,聆听时光深处的回响,在信息洪流里捕捉那些即将消逝的细微震颤。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这种倾听姿态本身,构成了温和而坚定的美学抵抗。
《且听风吟》的叙事结构呈现出“碎片化完整”。单篇散文常由看似离散的观察片段组成,却通过情感逻辑与主题共振形成有机整体。这种结构方式打破传统散文的线性叙事,更贴近意识流动的真实状态,也反映了当代人碎片化的认知方式。李劲峰的创新在于,他并未停留于后现代式的零散表达,而是努力在碎片中寻找隐秘的联结,最终拼合成一幅完整的心灵图景。
当大多数写作者在争夺读者泪腺时,李劲峰选择用理性的镊子夹起情感的碎片,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成就了文学感染力。他常通过记忆闪回、预感暗示等手法打破线性时间,在散文中构建多层次的时空结构。这种处理不仅丰富了叙事维度,更触及了人类存在的基本困境——我们永远生活在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裂隙中。“援藏两年,雅江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已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时空如何转换,雅江永远是我关注关心、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
李劲峰的乡土书写是明快的,充满激情。“天,蓝得那么纯净,像画家用巨大的画笔在天穹抹上一片蔚蓝,没有一丝杂色,朵朵白云似乎随风飘动在蓝色的天幕上。”(援藏记事《祝桑草原认亲》)。“岁月匆匆,时光荏苒,再次站在家乡的土地上,建武城已今非昔比旧貌换新颜。”(生活随笔《家乡的年味》)。
他的作品避免了廉价的多愁善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真实。只有多声部的叙事方式才能呈现乡村生活的复杂真相,超越个人抒情,从一口古井、一座石桥、一棵老树,展开对生命、死亡、永恒等命题的哲学思考,使作品既有泥土的芬芳,又有思想的锐度。
《且听风吟》展现了散文文体的自觉。李劲峰打破传统散文的范式约束,融入小说的人物塑造、诗歌的意象密度、戏剧的对话张力。“每次装订资料的时候,上面有许多回形针需要取下来。我看到有的变形了,有的生锈了,就随手扔进了垃圾桶。老李连忙去捡了回来,对我说:‘这些回形针恢复形状还可以用嘛,扔掉了好可惜啊!’”(“生活随笔”《老李》)。税收战线上一个税务干部、一个转业老兵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李劲峰建立了转换机制。他深挖兴文地区的文化矿藏、僰人悬棺的传说、苗族银饰的工艺、川南民居的特色,但这些地方知识最终都指向人类共同的生存命题。人生如茶,李劲峰是一杯乌龙茶,在《且听风吟》中留下淡淡苦涩的清香。
《且听风吟》以个人记忆为情感经纬,编织出一幅文学图景,将个人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在抒情与思辨之间,与时代节律同频共振。人人都必须经历的关隘,被作者转化为诗歌,唱给天下的男人听。把生活的艰辛,轻松愉快地转换为美食,喂养中年男性的味蕾。“我在家里看书看电视的时候,腰杆总是挺不直,女儿就经常批评我‘爸爸,咋个又把背弓起哟?老师说二天要成驼背哦!’老师的话我当然不敢违抗。”(“女儿成长记录”《小老师》)。
人生的一段插曲,温馨而香甜。
李劲峰的作品是散文还是随笔,已经不重要了。当代散文家积极探索散文写作的多重性,使散文写作向多元、自由的方向发展,散文作品无论在题材范围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形成了一道风景。散文与随笔同为散行文字,皆可自由抒写性情,然二者之别,犹春兰秋菊,各擅胜场。随笔可成散文精品,散文亦可含随笔风味。
李劲峰的作品大多数是千字短文,越短的文章越不好写,越考验作者的文字功力。文学的价值不在于题材的宏大,而在于观察的深度;不在于言辞的华丽,而在于情感的真诚。《且听风吟》印证了慢写作的力量。在这个崇尚速度的时代,或许只有慢下来,才能真正听见风中的低语,捕捉那些即将消失的微妙震颤。
《且听风吟》是一本不事张扬的原生态记录,低调而内敛。作者明白,“要想以从容的步履走好人生之路,至关重要的就是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做平凡人,干平凡事,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领略人生无尽的乐趣。”(“生活随笔”《喝酒那些事》)
李劲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且听风吟》,李劲峰著,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