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庞惊涛
高富华的《南京上空的孤鹰》,以扎实的史料考证与饱含深情的文学叙事,重现了中国空军首位王牌飞行员乐以琴的英雄人生。这部作品既是对抗战英烈的庄严致敬,也是历史题材创作中新闻纪实与文学审美融合的实践。从历史题材的把握到史料的遴选,再到新闻素材向文学艺术的转换,作品构建起多维立体的叙事空间,让沉睡的历史在文字中重新焕发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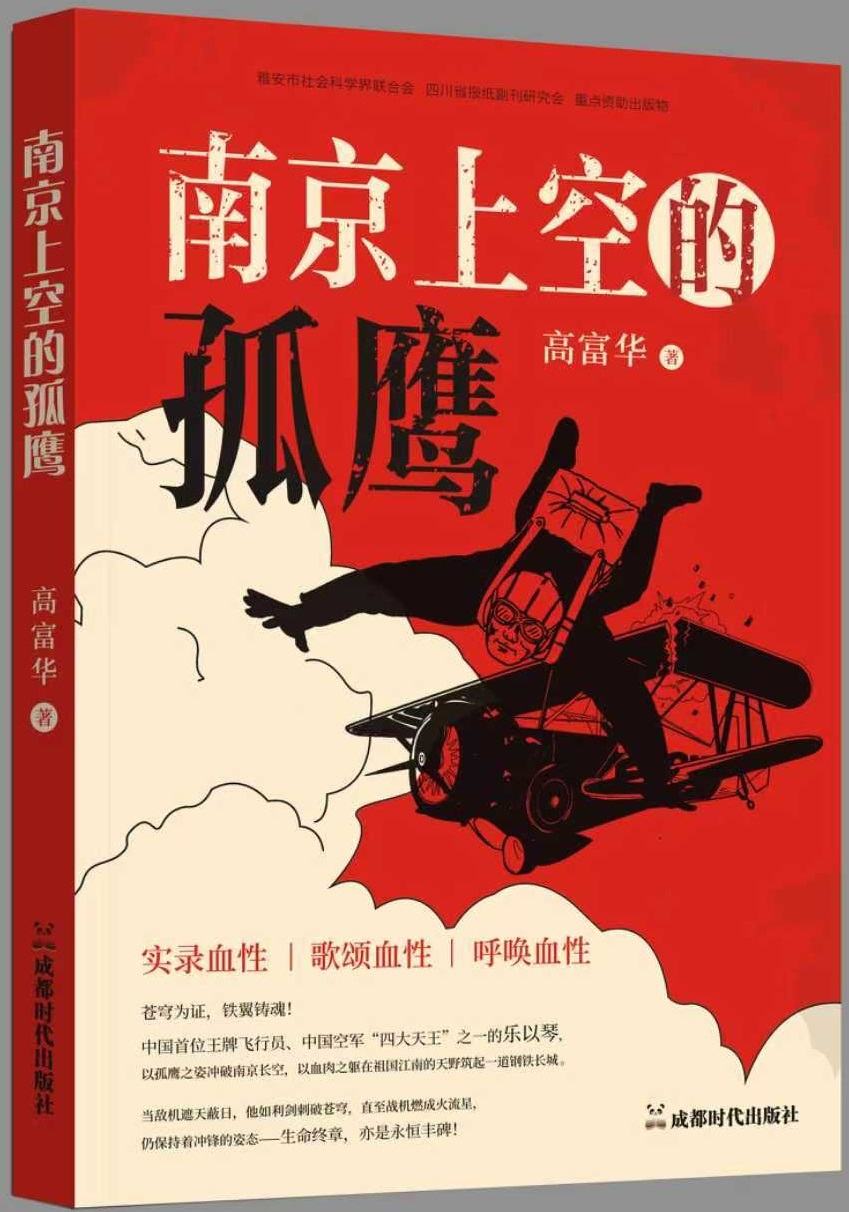
历史题材创作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在史实真实性与艺术表现力之间建立平衡,《南京上空的孤鹰》对此给出了回应。该书以时空折叠的叙事手法,将宏观历史背景与微观个人命运交织,既展现了抗战中空中战场的壮阔画卷,又刻画了乐以琴的成长轨迹。
该书以民政部公布首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切入,明确乐以琴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符号”的历史定位,随后回溯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南京保卫战的历史进程,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锚定英雄的生命坐标。
对历史细节的考证,该书体现出较为严谨的学术态度,不仅梳理了乐以琴从四川芦山走出的成长脉络,包括其家族耕读传家的家风传统、华西协合中学的求学经历,还还原了笕桥航校的训练生活、“八一四”空战的战术细节乃至战机型号的技术参数等。
尤其珍贵的是,书中对乐以琴7天击落6架敌机的战绩考证,通过整合《东方杂志》原始报道、战友回忆录、日军战俘供词等多源史料,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纠正了长期流传的战绩讹误,确保了历史叙事的真实性。
该书对历史语境的重建同样值得称道。
作者没有将历史人物简单标签化,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解读。如描写乐以琴报考航校时的内心挣扎,既展现了青年学子“宁为玉碎”的爱国激情,也揭示了当时中国空军“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的悲壮处境。
书中对笕桥航校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的反复强调,以及对1500多名毕业生壮烈牺牲的群体叙事,诠释了“无空防即无国防”的历史教训,使个人命运升华为民族精神的隐喻。
历史题材创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料选择的眼光与剪裁的智慧。该书在史料运用上展现出沙里淘金的耐心与点石成金的匠心,构建起多维度、多层次的证据体系。
作者历时10多年,从芦山县志、笕桥航校档案、旧报纸等文献史料,到乐氏家族后代口述、战友回忆录等活态史料,再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实物史料,全面打捞散落在时光中的历史碎片。最终完成了乐以琴的生命和情感塑造,使历史人物骨血丰满、可钦可敬。
在材料取舍上,该书遵循“典型性与细节性并重”的原则。对展现人物性格的关键材料,作者不惜笔墨,细致铺陈。如乐以琴在成都锦江大剧院痛击日本浪人的情节,通过“一拳打倒浪人”“鼻血混着怒火”等细节,呈现了英雄嫉恶如仇的刚烈性格;他在景德镇烧制“抗战瓷”时为亲人题字的细节,则揭示了英雄柔情的另一面。这些细节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经过艺术筛选的叙事元素,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增强了人物的立体感。
作品对特殊史料的创造性运用,形成了叙事亮点。
书中大量引用的家书、日记、回忆录等私人文献,如龚业悌《抗战飞行日记》中“我们队里没有击落敌机的仅有一两个人”的记载,乐以琴在航校学习时发出的“为了民族生存,宁可让我的身和心,永远战斗!战斗!直到最后一息”的誓言,以及王倬、吴鼎臣等战友的回信。这些带着体温的文字,打破了历史叙事的刻板印象,让读者得以窥见英雄内心的真实波澜。特别是逃婚求学的支线故事,通过家族史的侧面映照,丰富了作品的历史纵深,展现了时代变迁中个体命运的多样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史料的运用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
对存在争议的历史细节,如乐以琴牺牲时降落伞未打开的原因,该书同时呈现了战友回忆、史料记载等不同说法,既不回避历史谜团,也不妄加推测,体现了历史书写应有的审慎态度。这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性,为作品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史实基础。
从历史档案到文学叙事的转换,是《南京上空的孤鹰》最具艺术价值的探索。
作者有着多年记者经历,善于将新闻写作的真实性原则与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有机结合,创造出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感染力的叙事风格。该书在叙事视角上实现了从客观报道到主观体验的转换。作者没有局限于新闻式的事实陈述,而是深入历史现场进行沉浸式叙事。
在描写“八一四”空战时,作品交替使用飞行员视角(战机如雄鹰直冲云霄)、地面民众视角(看到膏药旗飞机坠落欢呼雀跃)、日军视角(中国飞行员竟如此勇猛),多维度构建起战场场景的立体图景。这种多视角叙事,打破了单一历史叙述的局限,让读者获得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
在语言表达上,完成从新闻报道到文学语言的升华。作者将新闻素材中的客观数据转化为富有张力的文学表达,如将“中国空军与日军战机数量对比1∶9”的史料,转化为“他们用不足300架飞机,对抗着如乌云般压来的2000多架敌机”的形象描写;用“栖霞山的枫叶红得像火焰,红得似鲜血”的文学语言,隐喻乐以琴牺牲的悲壮。这种语言转换不是对史实的背离,而是通过审美化表达,增强历史叙事的感染力。
该书对历史瞬间的文学重构,展现出叙事技巧。在描写乐以琴最后一战时,没有简单陈述“1937年12月3日牺牲”的史实,而是聚焦“孤鹰啸击长空”的最后时刻:“油箱起火的战机如断线风筝坠落,他选择延迟开伞避免成为靶标,却在距地面咫尺之遥时伞绳未能及时展开。”通过慢镜头式的细节刻画、心理描写与环境渲染,将历史记载中的冰冷文字转化为文学场景,让英雄牺牲的瞬间获得艺术生命力。
在叙事结构上,该书借鉴了新闻报道倒金字塔的结构与文学创作螺旋式上升的结构。全书以乐以琴牺牲的悲壮场景开篇,随后以“雏鹰起飞—雄鹰奋飞—孤鹰啸击”的三幕式结构展开叙事,每个章节既有新闻式的核心事实呈现,又有文学式的情感递进。这种结构设计既保证了历史脉络的清晰性,又形成了情感积累的叠加效应,使作品结尾的英雄追悼获得水到渠成的情感冲击力。
《南京上空的孤鹰》通过对历史题材的把握、对史料的遴选与文学叙事的转换,塑造了乐以琴这位抗日英雄的形象,为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借鉴。作品不仅让读者重新认识了中国空军抗战的悲壮历史,更通过英雄精神的当代诠释,唤醒了民族记忆。
总体而言,这是一部坚守历史真实、饱含人文情怀的作品。它提醒我们:历史不是冰冷的数字与事件的堆砌,而是由无数鲜活生命书写的精神史诗;文学不仅要再现历史的面容,更要传递历史的温度与力量。当乐以琴的战机编号“2204”在文字中重新翱翔,当“江南大地之钢盔”的美誉在新时代回响,这部作品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使命——让英雄精神跨越时空,成为照亮民族前行的火炬。
(《南京上空的孤鹰》,高富华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