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金翰
90位诗人为三沙写下的诗篇,由《诗刊》集结为《三沙,青春如潮》。诗集呈现了祖国各地诗人对三沙市独特资源的观察、海岛生活经验的书写和对海洋与人之间存在关系的体悟,构筑起海洋诗学图景。诗集道出的不仅是个人情感,更是千年农耕文明对海洋迟来的情书,恰似一座移动的文学灯塔,照亮了从以陆观海到以海为家的认知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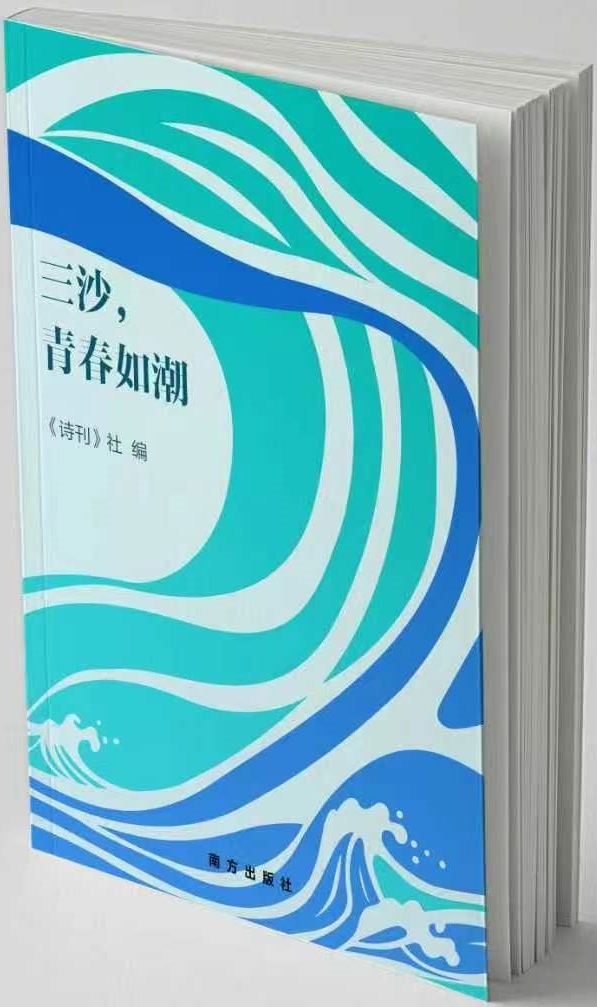
海洋诗写伦理
(一)海洋诗写转向
《三沙,青春如潮》(后文简称《三沙》)呈现的海洋诗学,其核心特质首先体现在书写伦理的转向。它内化于诗人感知海洋、言说海洋的具体形式中。
海洋之于诗人,从来不仅是外在风景。帕斯捷尔纳克在松林的静谧中,“竟时刻仿佛感到,/树干后某处是一片海”,道出大海作为一种内在召唤的普遍性。爱德蒙·威尔逊甚至断言,大海本身就是诗人生活的准则。
这种深刻的关联,源于海洋对感官与存在的直接浸染——当说出“海”这个词时,“突如其来的一片大海汪洋//展现在眼前,如同一声叹息一般”。咏叹调中的大海,交织着自然力、诗意与盐,天然地承载并融合着个体的生命经验与集体的认知体悟。
在《三沙》中,诗人们与海的相遇方式发生了关键嬗变。无论是“我”走向海边,还是“我们”航向南沙,流连诸岛,或从大海回返故乡,诗人都不再是隔岸“观”海的局外人,而是彻底浸入与海相关的“事件”之流。
“事件”,在此成为诗人们感知和言说海洋的核心媒介。它标志着一种诗写转向:海洋从被观察、被描述的对象,转变为诗人亲身历经、与之互动的事件;从吟咏、凝视与认识,转向具身性在场;从对海洋的抽象存在思考,深化为对个体与海洋共在之实存状态的体认。
“人类是陆生的……他生活,行动,行走在坚实的陆地之上。”这种以陆地为根基的视角,天然地将海洋置于客体和背景的位置。在《三沙》中,诗人们将海洋从与主体相对的客体背景升格为世界本身。人类在陆地上存在,也在海洋中存在。
李啸洋的《汉字生海》从语言文化基因角度,追溯“林、陈、黄、廖”等姓氏随中原衣冠南渡的轨迹,揭示了汉字血脉中流淌的海洋密码,暗示了人与海洋的“自然契约”——当人类真正承认并融入海洋的主体性,诗歌写作本身即是对这古老契约进行确认的仪式。
葛希建笔下“在南海种下一棵花椒树”的举动(葛希建《在南海,种下一棵花椒树》),让人想起古希腊人在黑海沿岸种植橄榄,将个体与文明经验扎根在陌生海域。
彭杰在《海岛纪事》中描绘永兴岛日出:“火红天使呼吸着银色的空气”。“银色的空气”让读者想到但丁《神曲》中对纯净天光的描绘,昭示着南海岛屿在诗人心中的光辉与神圣。
由此可见,海洋诗写的“事件”转向,本质上是诗人主体位置的变换——从岸上的“观”海者,变为海中的“居”海者、事件中的“在”海者。诗歌语言也随之从对客体的描述,转向对共同在场经验的言说,力求“通过向万物说话,让事物本身说话”。诗人也称为海洋事件的亲历者与构成者。《三沙》俯拾皆是的诗句,正是事件性的生动注脚。
“风已经把我的名字摘走/我还记得它曾经张望着——/黑夜的隧道贯穿了我的视线/他早已无缘/与我在黎明相见”(冯娜《夜航船》):个体被置于海洋夜航和偶遇事件中。
“日落的时候有人仍在海里玩水/我们已经坐下,观察在沙滩上捡到的贝壳……/唯一的浮标是闪烁的星辰/但在严酷的光芒过后/我们将被锻造为新的星”(苏笑嫣《到灯塔去》):诗句捕捉了从玩水、拾贝的具体活动,到“锻造为星”的宇宙哲思的转换。
“他们年轻的地址,是漂泊无定的船。/辛劳的水兵在等家信,信箱里/溢出那永无止息的风”(《頨譞《西沙邮局——一张旧照片》):“地址”与“漂泊”的矛盾,将守岛水兵的生存状态具象化为一个充满张力的、被风充盈的事件。
“阿喀琉斯却在流泪,远远地离开/他的伴侣,坐在灰色大海的岸边,/遥望那酒色的海水。/回忆她,就是注视一个被弃置的心灵”(车信昱《三沙小夜曲(组诗)》):诗句引用《伊利亚特》的典故,“酒色海水”成为映照“被弃置心灵”的具身化背景,历史情感在当下海景中复活。
“深海传出缓慢而具有磁性的音响/鸟喙将一种细长的寂静导入海水/时间本身变得略带颤抖”(蔡英明《鲣鸟起舞》):听觉事件成为感知海洋深度与时间质变的媒介,鸟喙的动作成为扰动海洋寂静、引发时间“颤抖”的关键。
“整个中午,舷梯都在喊/是巨轮的沉重/是大海的力量在让它喊”(李壮《寄南海》):“喊”赋予舷梯生命,人聆听的是海洋力量通过机械传递的呐喊。
“我们纯净地返回岸边/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仿佛/展馆里两块珊瑚的对视,我们想象海”(马欣雨《细细的,银线》):从海洋返回岸边引发对存在状态的反思,并通过珊瑚对视的意象,将“想象海”具象化真实的人和此刻。
尹马在《轻声说话的树》中写道:“向陌生人打招呼的树,作为/乡愁的长短句,在永兴岛/灿烂的街灯下,轻声说话”。树被赋予交流能力,成为乡愁的载体,在特定地点的“说话”行为,构成充满温情与地方感的微小事件。
陈航的《海边即景》捕捉瞬间:“海浪瞄准他的脚底,鞋子受了潮/秋风涌向少许的葱郁,头发流出昏黄”,一系列拟人化动词,将自然元素与人的身体细节紧密交织。
江非的《夜海》则说:“整座大海彻夜涌动的唯一原因,是一头鲸”,赋予海洋事件以生命本源的诗意想象。
王江平的《出门》呈现微妙体验:“许多细小的人群,/试图从我们身上分泌出去,/并带领着我们看见,波浪里现身的小岛”,将发现小岛这一视觉事件与身体内部的感受相连。
西渡在《椰树下的三角梅》中将植物置于“鸡的血冠”和“黎明”中,“相信爱,相信光,相信黎明”。
这些诗句共同编织“事件”之网,诗人的感官、身体、情感与思想皆在与海共处的“事件”中显现。
(二)海洋诗写话语
书写伦理的转向,往往催生新的话语表达。
《三沙》中的海洋诗写,展现出丰富的话语形态,共同编织着关于海洋的国家想象、生命哲思与青春记忆。臧棣曾辨析“存在”与“幸存”的诗学差异:“存在显示人,表现人;而幸存则化人,削缩人。”从诗意可能性看,“幸存把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减少到一种(即它自身)。”《三沙》诗群的实践,无疑属于一种丰盈的“存在”诗学。它超越“幸存”状态下对海洋单一化、外在化的“观看”,而是敞开在海洋中“存在”的多种现实与精神空间。
海洋诗写深植于民族的历史经验与集体想象中。无论是土地还是水域,现今的认知已超越以陆地为中心的、视海陆为冲突的空间秩序,海洋成为民族社会历史存在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祖国在此,有了颜色、气味、形状和声音”(李琦《南海群岛》)。
三沙的诗意书写从未脱离其历史语境,如徐威在《有一种神圣叫三沙》中凝视石刻:“比太阳更先发出光芒的,是驻岛战士于东兴/孤悬半空在礁盘上铭刻的四个大字。”刘笑伟在《描红》中书写士兵悬绳刻字的场景被赋予创世神话的庄严:“这块叫作老龙头的巨石/一定会想起自己五千年的沧桑/并在中国的南海边抬了抬头”。
历史的伤痕同样被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基石,如刘立云在《一个人和一面碑》中重构1946年张君然立碑事件:“他,张君然,一个区区上尉……当他在碑石上骄傲地刻下自己的名字/世界睁大了眼睛”。通过共同历史记忆的唤醒,三沙呈现了民族叙事中的“蓝色乡土”。
苏仁聪的《参观永兴岛》,将当下守岛与祖先的历史相连:“被大海耗尽一生的力量——我们的祖先/几千年以来,就是这样艰辛地生活在这片海”。一度的《春天的三沙群岛》,突出个体文化认同对家国意识的认同:“我身体里的界碑/有时,像国歌一样嘹亮/有时,像母亲的睡眠曲一样安详”。周琅然的《过赵述岛》则体现史笔般的冷静:“就像他在史书里那样,从未制造什么/聒噪的动静,甚至隐去籍贯与生平。”
此外,又如胡弦《从永兴岛到七连屿》:“我不能把这些小岛仅仅/比喻成项链,/就像祖国不仅仅是一位美人”;离离《蓝》:“我要的蓝,或者更高一点/像我在万朵云彩之上的祖国”;卢卫平《当我在纸上写下三沙这个词》:“用赵述、郑和、冯松柏/这些人名说出三沙”;卢文丽《永兴岛的鸟鸣》:“它叩问牡丹亭,拂过宣德路、北京路/点亮海上丝绸之路的邮驿”;陆辉艳《在三沙,万物是辽阔的》:“走入了天空和大海构成的蓝色圆心/那里安放着温暖的祖国”;宋晓杰《在夜里也能发光》:“是心跳,是骨肉……是祖国/是暗夜里的满天星斗”……这些诗句,均构成如今海洋诗写国家民族叙事的话语。
其次,是生态意识与生命共同体的觉醒。
诗人们突破传统“海洋—征服”的二元对立,开始建构一种平等对话的生命诗学。李少君那句宣告“我是有大海的人”(《我是有大海的人》),背后正是一种新型海洋伦理的生成。
杨不寒的《红脚鲣鸟》,将自然界的生存竞争置于悲剧性的崇高感中:“大海发出哀沉的琴音……而这片蔚蓝,已被它们认作永恒的墓园”,鲣鸟的生死与大海的蔚蓝共同构成庄严的生命场域。
苏笑嫣的《抗风桐》,则聚焦三沙特有植物的生态韧性:“像一株抗风桐,身体笔直/在这个光洁的沉沉白昼”。抗风桐,成为岛屿坚韧生命力的象征。
胡伟的《在海岸种树》则呼吁:“女人们不服气,她们站出来,种树种树”,这简洁有力的行动宣告,象征人类从自然的屈从者、征服者、索取者,向共生者的角色转变。
马睿奇的《海上摇篮》回归生命本源:“生命本来自水,来自晃动的环境/双臂作船的人,给婴儿秋千的梦”,以温柔笔触揭示海洋作为生命摇篮的永恒意义。
最后,是青春叙事话语的蓬勃展开。
《三沙》“青春”主题呈现出个体与集体的双重变奏。康雪的抒情主体以少女般纯真的姿态靠近三沙:“怀着满心的欢喜,和一种小小的胆怯”。这种细腻的个人情感的挖掘,准确呈现青年对陌生海疆的初体验。
李继豪在《三沙记忆》中,建构了一代人青春的集体印记:“朋友,海水竟可以这样蓝!/请珍惜即兴的咏叹”。“即兴的咏叹”捕捉了青春面对壮阔海洋时那份朴素的共鸣。
王江平的《三沙2号》,将船舱转化为一个观察海上社会的微型窗口:“我们趴在窗口,揪心于窗外的/这一场场角逐”。诗人在密闭空间中的凝视,揭示了青年人真实生存处境的一面。
迟牧的《置换关系》展现了更复杂的青年身份转换与融入:“异乡人,先品一口料峭的春吧/让与生俱来的砂石,在身体低处/归流入海”。个体“砂石”融入集体“海”的意象,喻示身份认同的转化。
又如蒋在超越现实的梦境:“我在那个夜晚/第一次梦见了天鹅 (《那个夜晚,第一次梦见天鹅》),还有液态的感官与流动的青春遐思:“夜在养育着/他们深处的皱褶/犹如/一次夏季的旷课/预告/汗渍湿漉漉地粘连肌肤/此时像/舒展了自身的女人”(《会有什么不同吗》)。
这些青春叙事,既饱含个体在青春时代独特的生命体验,也生动呈现海洋书写中集体的青春群像。
(三)海洋诗写主体
诗人们的“身体—世界”既有肉身意义上对海洋经验的情绪、知觉的具体经历,也处于权力分化和技术媒介中,后现象学承认用身体性取代原有的主体性概念,诗人在海洋中的知觉层面的身体感受,经由文化和技术层面的身体叙事,将身体转化为诗写主体,是“身体—世界”在和大海互动,创造语言。
当代学者认为,“身体和语言是创造性地相遇”,若“离开了身体的独特经验,语言的创造性是无从谈起的;照样,离开了语言的创造性,身体的经验也就不会获得有价值的出场空间”。
在知觉层面上,身体的感受主要通过感官调动实现。如廖亦奇的《37度蓝》创造触觉化的视觉:“原来海的颜色也有温度/和我一样/是37度”,通感修辞让诗人的认知始于感官交融。徐萧的《三沙野海滩嘉年华》记载触觉启蒙:“面对逐渐发黑的波浪,我愈发畏惧,/扭头看到女儿的笑脸,/我终于明白,海总是把一切简化”。孩童的触觉体验成为理解海洋的钥匙。
在听觉维度上,蔡英明的《鲣鸟起舞》谱写海洋生物声景:“深海传出缓慢而具有磁性的音响/鸟喙将一种细长的寂静导入海水”。冯娜的《夜航船》中:“波涛调低了它的声浪”。胡游的《榄仁树》则激活嗅觉记忆:“我闻到了枇杷的味道”,将南海植物与故土意象通过气味联结。
《三沙》诗集充满了对身体在海洋中变形、渗透与再生的奇妙书写,也是对身体经验的深度诗化过程。
如杨不寒在《白螺壳》中写道:“第一次,海水里坚硬的漩涡/开始了它奇妙的旅行。假我之手/到这苦雨的巴蜀”, 海洋之物经由身体媒介,完成从海洋到内陆的空间穿越。
阿垅的《海星星》:“我知道了,还有另一片/从海底伸出的天空/我知道了,还有别的星星/在白天也可以睁着传情的眼睛”,其身体经验浸透存在哲思。
阿天的《三沙行记》:“从三沙到海口,在轮船不停的摇晃中/大海短暂地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大海的律动内化为身体经验的一部分。
伯竑桥的《到三沙去》:“起初,我们在黑暗的舱室里卧着,一同渡海/像盒子里滚来滚去的几颗弹珠……人群欢闹后的夏天心事/剩在温热的滩涂/一架巨大、咸腥的、草莓味骸骨”,将渡海人群比作弹珠,捕捉密闭空间(舱室)中身体的被动状态。
迟牧的《永兴岛:清晨观海》:“感觉自己正在稀释,变得宽阔/而准确,像薄荷一样过活”,面对清晨之海的凝视,引发身体存在感的奇妙变化。
葛希建的《南海》:“一片海,神秘地守候在外面/曾经被遗忘的铁马冰河/在梦境里,将我无端地点燃,又浇湿”,海洋成为激发深层历史身体记忆的媒介。
黄舜的《三沙记》:“其中一滴,像词语不经意间/落到手心,离开时/身体于是像海螺,涌出无法克制的水”,微小事件触发身体内在海洋的共鸣。
李壮的《四人舱十四行》:“暂时我还醒着。掰不直的问号/先挂在鲣鸟的喙上寄存”,身体与精神的困顿,在海洋生灵处寻求暂时的安放。
刘博文的《三沙2号》 :“我的心脏是一口螺/里面有最胆小的寄居蟹/也有月亮牵起一整片海的浪花”,海洋生物成为内心经验的象征。
刘大伟的《对大海的再认识》:“她的沙滩,曲折而粗糙/珊瑚的断肢与掏空的螺壳”,是借身体经验引发的大海认知。
刘子睿的《珊瑚是大海的骨骼》:“你知道大海里什么最坚固吗/珊瑚是大海的骨骼……一个夜行人,他的骨头就像一副/滑落在地面的斗篷”,将珊瑚定义为大海的骨骼,赋予海洋以人的身体结构。
类似的身体经验,还有彭杰的《海岛纪事》:“鸥群梦中穿过你我的身体/落入黑暗的群屿”,苏仁聪的《走向大海》:“直到海水进入我的嘴里、胃部/才真正理解大海的苦涩和包容”,许淳彦《身体里的海》:“黑潮在腹腔涌动,逐一拨弄着弄堂、庙宇”,曳诩的《有一种蓝叫永兴蓝》:“永兴蓝,泛着干货店门口/深海鱼皮的,腥咸的香味”,周琅然的《八月十四日夜航南海无眠》:“我感到自己在/下沉,黑暗里有什么在搜寻我的眼睛”,杨依菲的《永兴岛主调:踏平坎坷成大道》:“当那永恒而宽广的某样东西彼时/流经我的血管,我感到我被放大,从一个人/被放大为所有人”,邹弗的《遇见笙珊瑚》:“嫩的手掌//用以肥沃自身。眼光覆盖/她后来无数次面对黄昏的场景”,车延高的《观海》:“没见过海的嘴唇儿/浪花哪里淘来的了荷尔蒙”,梁积林《永兴岛上》:“看一眼大海/我的肋骨呀已像一道道起伏的波澜”,洪光越的《海的献诗》:“退潮后的海把最裸露的肌肤献给了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诗歌技术延伸了身体感知海洋的维度,也重构了认知。
刘子睿的《珊瑚是大海的骨骼》重构我们的认知:“大海是一只忘记如何飞翔的鸟吗/水是它飞翔的记忆”,既呼应西方将珊瑚礁视为“海洋骨骼”的生态观,也呈现超越个体外“别处”的身体生命经验。
又如“一个岛屿在人们的望远镜里正在形成……它将有自己的名字,苔藓和。”(秦立彦《新岛屿》),技术作为身体的延伸,如望远镜延伸了视觉距离,技术视野拉近了人的身体和海岛的生存距离。
在《自动驾驶之蓝——给一位不知名水手》中,曳诩认为“蓝色是自动驾驶舱的小生态”,道出“蓝色”视觉借由航海技术成为“小生态”的箴言,技术媒介重塑了人对海洋的微观感知。
海洋诗学建构
(一)地方性与过渡礼仪
基于上述书写伦理、话语及主体的深刻变革,《三沙》最终指向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海洋诗学的整体建构。这种建构主要体现在对存在关系的重新理解、对人类经验的探索以及对抒情传统的反思中。
梅洛迪·朱曾提出“海洋即媒介”观点,将海洋环境本身的物质性纳入认知范畴。压强、盐度、浮力、光线等物质要素“为人类知识的形成提供了认知制约”。狄金森的诗句“到处都是银色,/沙绳将其束缚,/以防它抹去/那条被称为陆地的轨迹”,即捕捉了陆地和海洋之间隐含的制约关系。
诗人们的海洋书写,往往会经过陆地景象的过滤,如梁平在《进入我身体的海南》中自白:“我的私心杂念渐渐长成一座山/山长出了五指”,心中陆地的山脉与海洋是相互渗透的节点。
传统的地域性概念是地理中心主义的,如“英国性”曾被视为“显著的民族生活特征”,单纯的“地理性”“英国性”,让人们的思想深度停留在“幻象化的空间”中,其界定往往隐含着排他性。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杰提出的“非地方”概念,虽强调了流动性,却暗示着身份的临时性与意义的匮乏。
《三沙》诗学则指向“开放的地方性”:它不再执着于固定的地理边界或文化符号,而是根植于个体在特定空间中的真实生存经验、身体感知与情感投入,面对的是“灵魂深处的真实”。它要求诗人以开放的身心去体验、去沉浸生活。这种“开放的地方性”体验,常伴随着深刻的“过渡仪式”感。
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哲乃普认为:“无论是个体在一生中还是群体在生存发展中,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都时时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特别是在两个精神世界(即平凡或世俗与神圣或宗教)之间的过渡。”此间,“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行为方式。”在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之间,海洋航行、登岛体验,海陆经验的转换,对许多来自内陆的诗人而言,是一场充满阈限性的过渡礼仪。
符力在《寄自七连屿》中写道:“你买了这张普普通通的明信片,/只花了几元钱。”“明信片的背面,我盖了一枚印章,/还写了你的名字。/我抚摸你名字的时候,南海的风,/也抚摸了我。”
又如胡游的《在鲣鸟俯冲的地方》:“站在船头/飞鱼分开整片的海/一万里后,我默许它重新相连”,葭苇的《海心沙》:“站立——/和这一秒相续的/是我们下一秒必须的移动。/没有更远的去处”,吕周杭的《椰子》:“你抱着椰子给我,像某种幸运的/交接。仪式如此简单”“远处祖国母亲敞开她的手,/大理石般坚硬,直击海的眩晕”,彭杰的《海边的夜晚》:“我与七连屿共同前行,/却从未相互走近”,苏仁聪的《在永兴岛的一个傍晚》:“无论怎样我都习惯生活在陆地,岛/是很小的陆地”,朱弦的《回赠》:“收到大海的明信片,回赠友人晚霞/以及柳絮”,北野的《向三沙》:“我们要在大海中建一座庙/它金碧辉煌,摇摆不定,众神欢腾/上面挂满我们心中的灯盏”,韩玉光的《永兴岛的风》:“每一个下海拾贝/伞下垂钓的人/都是尘世中幸福的人”。
诗人们在日常身体经验和海之间进行的行为仪式,建构了“流动的地方性”的海洋诗学话语。
(二)栖散性与人类诗学
在海洋中,“栖居”呈现出“栖散性”特征——一种在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中真实的存在状态。“栖散”不同于前文的“非地方性”,后者仍是大陆经验界定下的,且不指向“居住”而指向“流失”。人类对存在的认知传统,深深植根于陆地经验。
“大地是承受者,开花结果者、它伸展为岩石和水流,涌现为植物和动物。”人在世界中的“逗留”词源指向陆地居住。其希腊词根“geo”意为“土地”(land),生活于“地球”而非“水球”的文化偏见深植于意识底层。
然而,海洋从未在人类精神版图中缺席。它构成“熟悉又陌生”的形象序列,如北欧神话中的克拉肯、《圣经》中的利维坦、美索不达米亚的提亚马特、中国的龙王、希腊的波塞冬等,昭示着海洋那不可驯服的原始伟力与神秘诱惑。
英文短语“at sea”捕捉了人在海上经历的“迷失”感。这种“迷失”催生了一种复杂的“处所意识”,揭示了人与地方的关系并非总是段义孚描述的“恋地情结”,同样可能充满焦虑、迷失与在未知之处重新绘图的冲动。人可能真实居于随时变动的具体生命状态中,无论是风景、照片、心绪、梦境等,都是呈现赤诚生命的实存,并引发人们重新绘制新的经验,构造新的世界。
阿信的《在大海边》如此说:“椰风和潮汐的声音,栖满双耳。/想起雪落高原/风过松林,马匹”。
李元胜在《过三沙北礁》中沉思:“我/只不过是一个丢失了大海的人”“我不过是一点点/它溢出的部分”。
蓝格子在《生活一种》中,呈现微小而坚韧的生活操持:“针,值得信任的尖锐之物/缝补。持有生活的一种最佳方式”。
李继豪在《一轮明月》中写道:“我们总是看到一轮明月/……/写进一首诗里/模拟它的光晕和轨迹……看,一张新照片/一个无比具体的时刻/四个人背对着它/四个人朝向不同的风景”,恒常的“明月”与“一张新照片”记录的“具体时刻”并置,“四个人”背对永恒,而不同朝向,是栖散性群体关系的微妙写照。
马馨的《水生》,重新建构个体在海洋中的经验:“你如海鸟,双双开辟此刻的阒寂/向代代继存去/你吐出生民与丰收的出口”。
树贤的《天倾西北》,将个体心跳与古老神话关联:“但我依然保持着一颗浸润过海水的心脏/当这颗心抵达三沙的时候/它便找到了当初地陷东南的海水”。
此外,还有很多诗句呈现了人在海洋之中的“栖散”状态。
如玉珍的《海上》:“我们在一片溅湿的蓝色中站着……蓝色的艺术使人突然深沉”,李浔的《西沙海螺》:“它们和海螺的声音一起/已开在了我的耳上”,娜夜的《浮力》:“漂在海上的人/心事终于沉到了海底”,沈苇的《赵述岛》:“透过礁石洞,看见永动机和瓦雷里:/‘……大海永远在重新开始!’”,杨克的《南海海眼》:“目睹明代赵述的宝船 /和我今天乘坐的小艇,被同一个风暴/喊住。前行是涛声”,杜绿绿的《观海》:“讨海的人们,/穿梭于浮标、竹竿间,一艘小船/正在书写不为陆地人所知的/霞光故事”,黄礼孩的《岛屿》:“它是自然放养在别处的野马,它的鬃毛/在黄昏的夕光里,在辽阔的海洋上疾飞”,叶玉琳的《两个我》:“请允许我用第三只耳朵/倾听它们的声音”。
当人具身于“海”的“事件”中,其写作也实现从自我到群体到人类的过程,充满人类学视野的思考。这种人类学诗学避免现代文明科学话语的影响与建构,“尽可能带有感性完整和丰富地呈现原汁原味的”文化经验,为读者呈现在大陆从未见过的海洋(海岛)生活图景。
伯竑桥的《到三沙去》,记载了独特的味觉仪式:“海草和鱼干同嚼/有近似新鲜折耳根的味道”。
赵茂宇在《在灯塔下卖金枪鱼的男人》中写道:“他的头发爬上了蜘蛛,背影旁边/有蜘蛛吃过的西瓜,持续是软衣服”。
邹弗在《遇见笙珊瑚》中构建海洋神话:“她的寂静在发散。一个黄昏/壳里流出星空”。
陈均的《宝船》则说:“在白色海涛闲话里寻一个迢迢/路途里躺在翠绿的懒人树下/吃椰子的人”。
年微漾的《在南海》,唤醒民间信仰记忆:“一百零八位/兄弟公,对应天上星辰”,将渔民守护神纳入诗歌宇宙。
王夫刚的《手抄本更路簿》,更成为非文字传统的纪念碑:“晚年的更路簿/应该享有跟晚年的船只和晚年的船长等同的礼遇”。
杨章池在《三沙,蔚蓝的绽放》中写道:“郭守敬凝神着他的高表,反复比画着简仪和仰仪。/郑和留在图册上的墨迹,一直指引/那些刻碑的,升旗的先人们”。
胡伟的《在海岸种树》,书写当地海畔生活经验:“她们,一个村子的女人去海边种树/扒开沙子,放进木麻黄的树苗”。
(三)消除自身与新抒情主义
现代社会中的自然概念是被后天建构起来的,劳伦斯·布伊尔提出过“新环境美学”的概念,认为语言应摆脱自我指涉,而增强对外在自然的指涉,语言作为“古老的象征符号体系,它指向外部的、实实在在的客观世界”。
这种意图在于让人们看清一个事实:由于语言对自然的翻译,语言建构的自然是带有意图的,它并不是自然本身。如西方的田园诗中具有隐退倾向,有田园乌托邦的建构,也有从阶级、性别、生态等方面对田园之自然进行阐释。自然往往处于社会结构、历史话语中,是后天形成的自然。
与之相对的,是李少君的诗歌生涯中有一个经典事例:“……我一直以为自己过于理性, 写不出诗来。可是去年底(2006年)突然有一天,我去黄山开会,住在新安江边的一个旅馆里。深夜出来散步,正好细雨蒙蒙。我看着烟雨迷蒙下的新安江,显得格外宽阔,河水浩淼,一条大河似乎是从天那边蔓延过来。我突然心里一动,看着蒙蒙细雨,就想:要是几百年前,这里该是一个村庄,河流流到这里,村庄该有一个码头,古时叫渡口。于是想到一句‘一个村庄,是一条大河最小的一个口岸’,然后,我的脑子好像一下打开了,豁然开朗,我就这样想着,就这样写出了一首诗……叫《河流与村庄》……”
李少君创作《河流与村庄》的经历,为超越这种话语建构提供了启示性个案。诗歌灵感源于身体完全沉浸于环境“事件”所触发的即时、朴素感知与历史想象的交融。这是一种“消除自身”后,让位于环境、历史与身体所处“事件”本身的体验。
“消除自身”并不是消除自我的情感,而是呈现为以下形式:一者是将个体自我升格为“泛神”意识,如李少君曾在诗歌中写道:“我是有大海的人/我的激情,是一阵自由的海上雄风/浩浩荡荡掠过这一个世界……”(《我是有大海的人》),“我们率领着一支鱼的混合部队/在大海上劈风斩浪,勇往直前”(《在海上》)。“我”确证的是大海的自然伦理,在世界和“我”之间实现“人诗互证”。另一者则体现为走出自我、成为他人他事,让自我消失的他者意识。他者意识“要求一个人有勇气消除自我,以便能够发现他者的存在”。
在《三沙》诗群中,这种“消除自身”以感知海洋他者的努力清晰可辨。
司文在《珊瑚屋》写道:“姐姐,我不是一片好珊瑚”“姐姐,我们不做珊瑚石”“回到海底,去做人鱼的铠甲吧……埋下头/在水波中消失”。作者反复的自我否定和主动选择“消失”于“水波”,体现了主体有意识地“消除自身”人为属性,以期回归海洋本源。这是对海洋他者力量的敬畏与归附。
谈雅丽的《长风吹袭》中:“你呼唤我一声,我就分海为路/化身渔船上温柔多情的,珍珠姑娘”,响应海洋的呼唤而“分海为路”,并“化身”为“珍珠姑娘”,主体消融于海洋神话谱系,成为其一部分的浪漫想象。
又如徐萧的《三沙野海滩嘉年华》:“大风,吹过坚硬的事物,又继续吹皱/我们的脸,把海的语言捎至/唇齿”,主体在接受中学习“海的语言”。
许淳彦的《三沙,记一个晕眩的梦》写道:“鱼鳞还未从皮肤上剥落吗?世纪前的海床/黄昏搁浅”,“鱼鳞”“皮肤”暗示一种未完成的人鱼变形或海洋印记,个体存在在宏大的海洋时间中模糊、消散、“晕眩”。
杨金翰的《近视镜》则说:“海风试图吃掉我们的手臂/影子瓷器般碰撞/学鹦鹉争相重复感叹”,海风“吃掉手臂”具有侵略性,人影脆弱如“瓷器碰撞”,人声是无意义的“鹦鹉重复”,呈现个体的人瓦解、失语状态。
叶娟梅的《灰尘》:“我连同我脚下的岛屿一同变成了一粒尘埃”,将自我与岛屿共同降格为“一粒尘埃”,这是面对海洋无垠时对个体存在渺小性的极致体认。
余退的《在礁石上》将人喻为“掠过海水的蝴蝶”,强调其短暂、轻盈与易逝;“垂钓者”化为“暗的灯塔”,则是主体在专注中将自身化为海洋景观的一部分,成为沉默的导航者。
赵茂宇在《在灯塔下卖金枪鱼的男人》中写道:“所有皮肤消失之前/灯塔上的买客回来了”,暗示一种存在的临界状态(暮色或死亡),而“买客回来”则是海边日常生活的延续。
这种“消除自身”的体验,导向一种新抒情主义的可能:它不再是浪漫主义式的自我膨胀,而是主体在海洋的宏大与深邃面前,通过消解自身的傲慢,重新寻找与自然、历史对话的基点。
白庆国的《一个来到大海的内地孩子》,捕捉到面对海洋时的失语与敬畏:“他不知道发出怎样的声音才能与海浪的声音匹配/他禁言着,望着大海”。
燎原的《落日观察》,呈现了自然伟力对主体的吸纳:“这时候翔集的鸥鸟一起朝它飞去/天地一瞬间被抽空”。
树才的《大海》,道出感知的极限与超越:“所见使我失明/所闻使我耳聋”——极致的感官冲击,反而导向某种超越感官的领悟。
汤养宗的《大海的声音》,坦承个体在大海面前的无能为力:“一生对大海模仿与剽窃/学习它说话。一生也说不出一句自己的话”。
意寒的《回声》,则点明了书写作为“消除”后的精神远行:“写,就释放一种远行的气息”。其诗《橡树林》则以更内敛的意象,收束了远航与宽恕的主题:“前行的路已被洗净/挥手告别,代表最小尺度的宽恕/我们的呼吸是一个圆/正飘向共同沉默的头顶”。离别是一种恩赦,作为群体的我们,吞吐的不过是循环而轻盈的静默。上升至现实经验以上,指向“消除自身”后可能抵达的宁静与存在。
宁静到,“就像一个所有东西都沉没了的地方,就像一种空气的稠密,就像一种空无的满盈或沉默的窸窣。在所有物和存在者毁灭之后,只有一种无人称的实存之‘力场’……”海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无人称的实存之力场”的具象。
意大利诗人蒙塔莱曾叹息道:“爱是未完成的潮汐。”而《三沙》的诗人们,以集体的、具身的、充满历史与生命意识的写作,努力让这“潮汐”趋向完成。我们就是世界上“最美的溺水者”,叹咏在逝去时光的海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