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朝
我们为什么读诗?为什么写诗?在文化视域,很多评论家都有着深刻的见地。在诸多文学体裁中,诗歌之所以能孤峰独秀,在于其首先的语言美学意义,其次是思维创造、言志抒情、提升品质、传承文化等价值。诗歌是文学的极致表达:语言之美感、意象之多姿、立意之深邃、空间之多维。
任何时代,诗歌都不会泛众化,即使是盛唐。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勃兴,也只是基于为数不多的思考者的催发。那些以语言缝合理想与现实裂痕的诗行,因慎独、觉醒、反思、教化,所以可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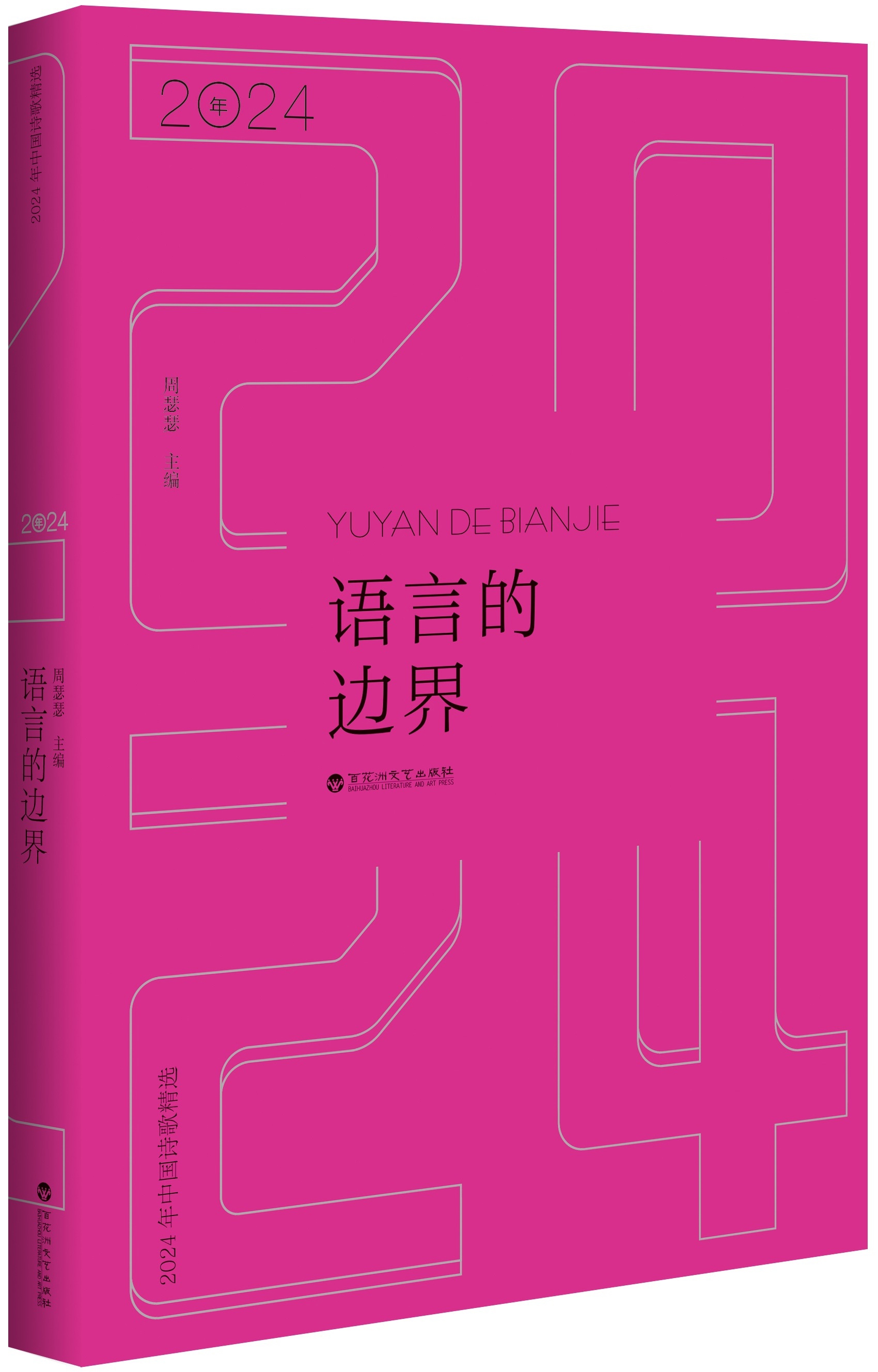
很显然,这些都归功于语言的创造。因由文字和语言的无限发掘与编排,才有了诗行的节奏、韵律和内蕴。这也正如周瑟瑟在其主编的诗集《语言的边界:2024年中国诗歌精选》序言中所说:当我提出“语言的边界”,实际上承认了我们想象的边界,但,想象是没有边界的,也就是说语言没有边界。如果有边界也只是暂时的,只有人类认知的边界,想象的贫乏决定了语言的边界。诗是想象,诗可以突破想象的边界,从而获得语言的恩惠。
语言没有边界,想象没有边界,诗学没有边界。优质的诗歌文本从来都是诗人置身于生活的繁冗时空,对现实进行深度思考、辨析、解读,在冲突中博弈,在博弈中建构,并突破语言的边界,呈现出可资鉴赏的诗歌意境,让读者沉浸于特定的景深,获取有价值的阅读感受。因此,良正的诗歌文本不仅内涵丰蕴、节奏明快,更兼具艺术审视和美学感染意义。
毋庸置疑,现代诗歌语言的演进是一个充满变奏的过程。从上古歌谣至《诗经》,至《汉乐府》,至唐诗宋词,再至现代新诗,承载了传统文化和东方情感的诗歌语言,是历代诗人首要的淬炼功课。“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即是诗人为遣词造句而苦心孤诣的见证。
读一首诗,就是阅读文字深处的诗人,读诗人的经历、认知、智慧、思想。每一位诗人,都会在字里行间留下行走或思考的影子,都会在无意间把自己叠加成多重意义,并呈现在文字中。因此,好的诗歌作品,让读者撷获的不仅是文字的丰盈、结构的美感,更多的是得到触动、力量和催化。
刘川的《治愈》一诗,暗示诗人的创作如同“护士”客观记录诊断日志。这种医学术语的艺术处理,体现了文字的诗化重构。文本最后一句“病人化为医生”,看似悖谬,实则蕴蓄深意,暗含世象的积弊抑阏以及诗歌拯救价值的哲理性思考。
《语言的边界:2024年中国诗歌精选》将女性诗歌以“真的尺度”呈现,这也是对近些年女性诗歌愈发活跃与斑斓的集束观照。女性诗歌的多元气质,昭示着新一代女性的觉醒与思考,不论是语言层面,还是结构层面,甚至立意层面,女性诗人群体的担当、真格、空灵和通透在诗行中得到了彰显。
相比成年诗人作品语言的成熟、冷静和理性,囿于阅历和视野,孩子们的诗歌语言显得尤其率真、活泼,大多直抒胸臆,但不乏超凡之语、新奇构思和深层隐喻。13岁的海菁写道:“姥姥从冷柜里拿出一条鱼/鱼死得好冷”。只有两行诗句的《冷》,以日常口语化的文字表达,用最少的文字注脚万事万物的死亡命题。冷,即是物理属性,也暗喻对死亡的情感认知,在诗行的“飞白”中充满关爱和疼痛。
诗歌最初的表象是语言,语言的深处是立意。没有好的语言支撑,诗人很难将内心感受灵动、形象、准确地付诸于文本。良好的语言建设能力,是诗人必备的基本素养。优秀的诗人往往能对关注的事物,特别是对那些深具内涵的重要事物,通过观察和感知,然后以独自的敏感和创造力,使用富有感染能量的特色语言表现,让读者产生共振和共鸣。
周瑟瑟以诸多诗人及其文本为研理对象,主编的《语言的边界:2024年中国诗歌精选》,辐照出当今诗学的语言质地、创作现状和思考向度。从纷繁的字里行间,析解诗歌的语言特点和文化内涵,建构诗学的现场实践和理论体系,为中国诗坛提供了见识和经验。
语言没有边界,诗歌没有边界。那些生命的启示和文化的底细,一直都在我们的语言深处。
(《语言的边界:2024年中国诗歌精选》,周瑟瑟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5年4月)
作者简介
周朝,本名刘林,诗人、作家、资深传媒人。创作现代诗歌、文化随笔、历史散文及文学评论,著有文学作品集《观照乡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