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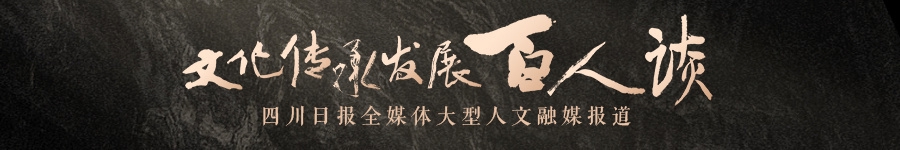
(点击图片进入报道专题)
人物简介
赖声川,台湾剧作家、导演,表演工作坊、上剧场创始人,乌镇戏剧节发起人之一,会昌戏剧小镇戏剧、南京新剧荟发起人。现任上海上剧场和台北“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乌镇戏剧节常任主席和评委会主席。
自1984年以来,赖声川的舞台作品从台湾出发,创造新型现代剧场形式,深切广泛地影响了华语世界的剧场,代表作包括打开台湾剧场创作新时代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1985年),被《纽约时报》誉为“当代中文剧场最受欢迎的作品”的《暗恋桃花源》(1986年),以及八小时史诗巨作《如梦之梦》(2000年),以及与《如梦之梦》共同被称为“双峰”的《曾经如是》(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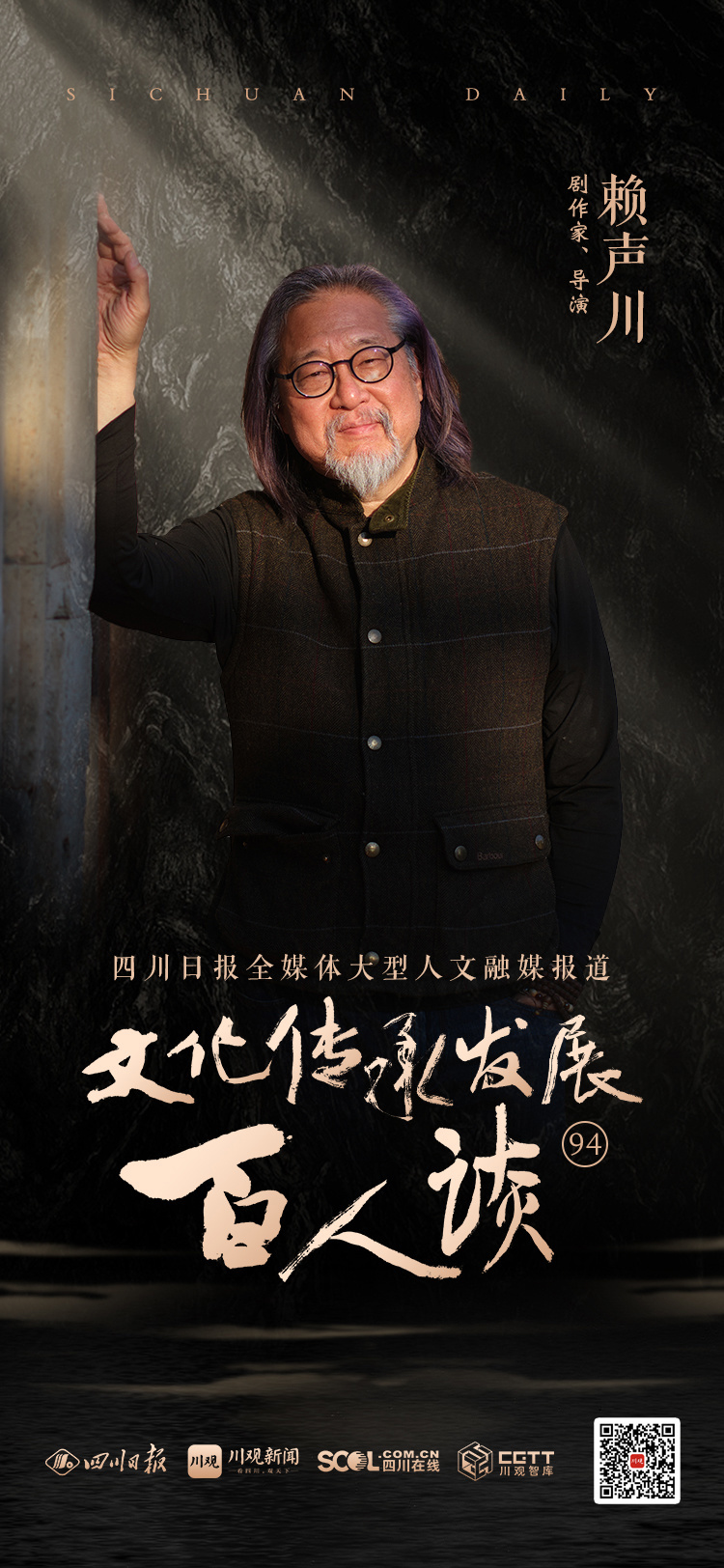
●戏剧是用情感记录时代,这种记录比单纯的事实罗列更深刻
●拥抱创新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为了追求新而新,因为重要的是好或不好,强烈或不强烈,以及传达的意念清楚或不清楚,这才是重点
●文化生态就是让一个地方的文化基因活起来,创意和产业是自然生长的结果,不是刻意追求的目标
●四川的戏剧人也可以从“小”做起,去把本土的故事变成剧,哪怕是小剧场演出,也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故事里有“四川的味道”,是外人写不出来的
四川在线记者 田珊 摄影 吴枫
8月16日,当第348场《宝岛一村》的大幕在成都城市音乐厅歌剧厅缓缓落下,台下观众的掌声与泪水交织,震撼与感动交汇。村口大树下几十年如一日的“争论”,铁皮屋蒸笼里溢出的包子香味……穿越半个世纪的眷村记忆,在蓉城续写感动篇章。四代人、三个家庭的故事,不仅让无数人想起自己的“根”,更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戏剧的无限可能。而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名字——赖声川。
40余年的戏剧生涯,他创作出了《暗恋桃花源》《如梦之梦》《宝岛一村》等不可多得的佳作,也倾注心血打造出台北“表演工作坊”、乌镇戏剧节、上海上剧场、会昌戏剧小镇等戏剧生态圈。
赖声川的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碰撞的节点上,最终在中国戏剧的土壤里,培育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果实。

赖声川和川观新闻记者
成长烙印
跨文化土壤里的戏剧萌芽
如果要聊赖声川的戏剧创作,就一定避不开对于中西文化语境的探讨。“我的成长轨迹和大多数人相反——别人是从本土走向海外,我是从海外回到华人社会,这种‘反向旅程’决定了很多事。”赖声川的成长经历,在中西文化的交织中跌宕起伏,为他日后在戏剧领域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他能够站在独特的文化视角,创作出一部部经典之作。
1954年,赖声川出生在美国华盛顿。父亲赖家球祖籍江西省会昌县,从事外交工作,母亲屠玲玲出生于宁波书香世家。童年时期的赖声川,身处西方文化的浓厚氛围之中。在华盛顿的校园里,他接受着西方教育,而家庭氛围中则不乏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在赖声川的记忆里,父亲会用毛笔批写英文公文,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制作的真丝灯罩曾卖到白宫。
12岁那年,赖声川随家人回到台湾。刚回到台湾时,文化冲击带来的阵痛如影随形——由于学习体系和语言变化的影响,在美国因资优两次跳级的他在台湾却赶不上学习进度;生活习惯和文化氛围方面,西方的自由奔放与东方的含蓄内敛形成鲜明对比,也让赖声川在适应过程中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但正是这种冲突与碰撞,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对“身份认同”的深刻思考,也成为他往后创作中被反复探讨的重要命题。
1978年,赖声川远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戏剧系深造。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台湾辅仁大学英文专业学习了一段时间,对西方文学有了一定的积累,但真正系统接触西方戏剧理论,还是在伯克利的课堂上。当时,后现代戏剧、实验戏剧正在西方兴起,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格洛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理论,像一场思想风暴冲击着他的认知。甚至,赖声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专门将其中一章留给了贝克特,并为此阅读了贝克特的几乎所有剧场作品。
但这种冲击并没有让赖声川全盘照搬西方戏剧手法,反而让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位置”。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经历,让赖声川拥有特别的能力——既能快速深度融入社会,又能随时抽离观察。“我在台北夜市吃小吃、在成都路边用餐,那种自在感不输给本地人;在旧金山看球赛,和观众一起为球队欢呼、吃热狗,我也能完全投入。但我能突然‘跳’出来——比如看到成都马路上交通拥堵但是司机们却很少焦躁,我会觉得人们身上的这种松弛感非常有趣;在国外球场,我会思考‘星期三下午5万人看球,大家都不用上班吗?’”
这种“融入+抽离”的视角,也让赖声川更清楚自己的文化根脉。对于“我是谁”“我到底是哪里人”,赖声川的回答是:“我的答案在我念初中、高中、大学那些年就已经很清楚了,我是中国人,我内心真正认同的是东方的、亚洲的文化内核,希望传承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根脉。”
理念成型
“表演工作坊”的诞生与“集体即兴”创作
1983年,赖声川在伯克利博士毕业后带着一腔戏剧创作热情回到台湾。“我回来后发现,台湾观众需要的不是‘西方的复制品’,也不是‘传统的复刻版’,而是能反映他们生活、情感的戏剧,真正属于‘当代台湾’的戏剧作品。”于是,他萌生了创立一个“不一样的剧团”的想法——这个剧团不依赖单一编剧,不局限于固定模式,而是让演员、导演、编剧共同参与创作。1984年,“表演工作坊”在台北正式成立,而它的第一个“实验”,就是《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这部作品的诞生,源于赖声川的一个大胆设想:将中国传统的“相声”与西方的“情景喜剧”结合起来。当时,台湾的相声已经逐渐式微,年轻人很少听;而西方的情景喜剧虽然受欢迎,但缺乏本土文化内核。赖声川决定取两者之特色,让演员从“生活观察”出发,用“集体即兴”的方式创作。这部作品一经上演,就引发了轰动。剧场里座无虚席,观众们笑着笑着就哭了——因为剧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像在讲自己的生活。而“集体即兴创作”这个看似“混乱”的方法,也第一次展现出它的魔力。赖声川解释:“集体即兴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从生活中来。演员们都是生活的观察者,他们的经历、记忆,就是创作的素材库。而我的作用,就是把这些素材串联起来,找到其中的情感主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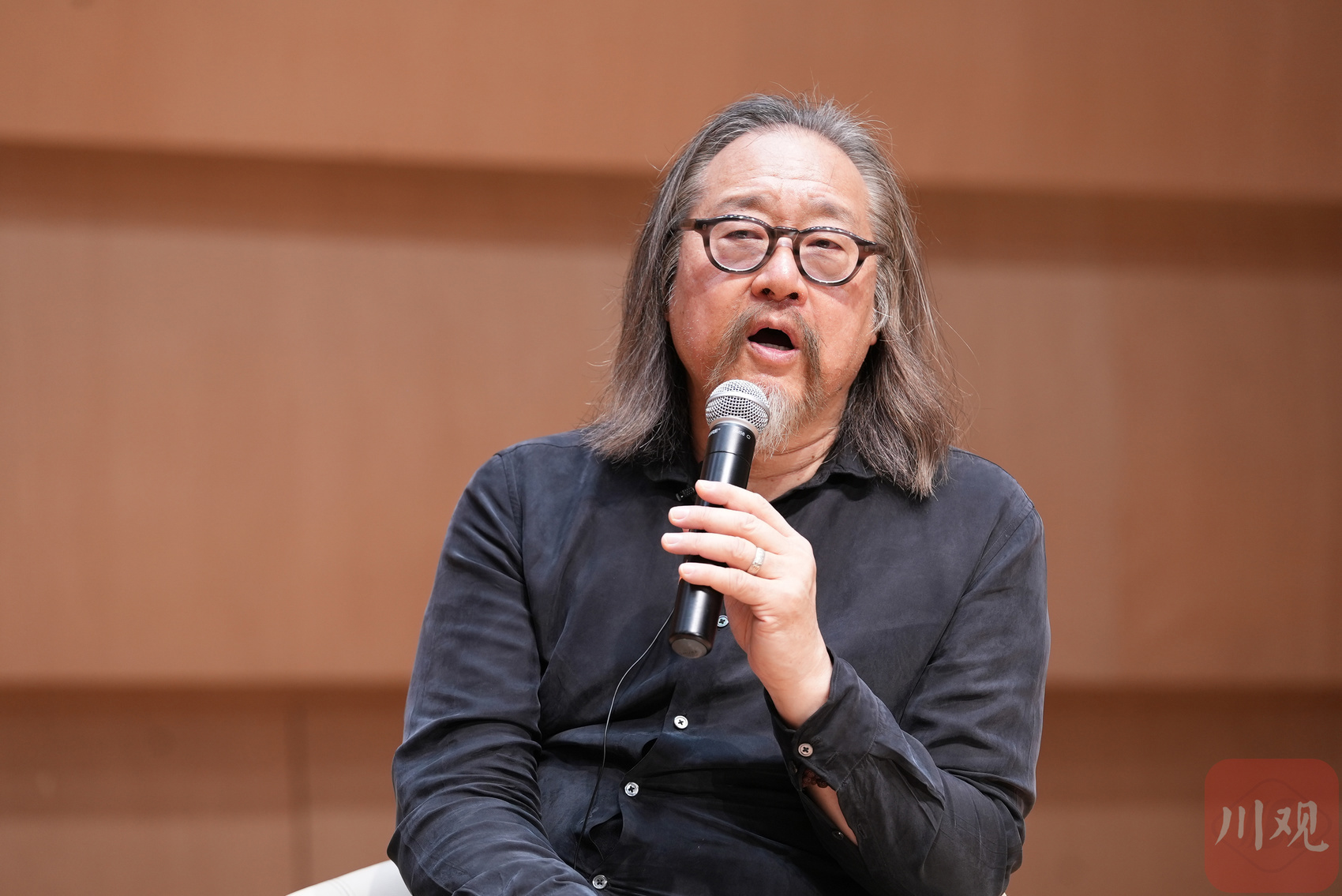
赖声川接受四川在线记者采访
而后,即兴创作不仅成为“表演工作坊”的核心方法论,在赖声川其他戏剧作品的创排过程中,他也始终鼓励演员能够即兴创作。“比如,在《宝岛一村》的创作前期,演员拿到的就是一个大纲,我只告诉演员要传达的内容是什么,说什么词、如何表现,现场来反应。”在采访中,赖声川还揭秘了《宝岛一村》中的名场面——“钱奶奶教朱嫂做天津包子”:“天津包子怎么做,大家都不知道。‘肥瘦肉的比例需要随着季节变化,夏天三比七,冬天四比六’,这些其实都是我现场编的。”
“集体即兴创作的本质是信任。”赖声川强调,“演员要信任彼此,信任观众,更要信任生活本身。因为只有从生活中提炼的情感,才能打动观众。”这种理念,也让赖声川的戏剧作品更加有温度,无论是《宝岛一村》里的眷村烟火,还是《如梦之梦》里的人生轮回,都能让观众在剧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表演工作坊”也从一个小小的剧团,逐渐成为华语戏剧界的“标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戏剧人。
文化传承
在“守”与“变”中寻找中国戏剧的未来
如果说“集体即兴创作”是赖声川戏剧的创作方法论,那么文化传承就是他戏剧的精神内核。在他的作品中,总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但他从不简单地复刻传统,而是用不断变化的视角重新解读。
在《如梦之梦》中,他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环形叙事”结构——故事从一个医生的视角开始,然后转向病人的人生,再转向病人讲述的另一个人的故事,像一个“轮回的圆环”。这种结构让人仿佛看见《红楼梦》“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独特结构,而现代的舞台设计,让观众坐在舞台中央,演员在四周表演,又营造出沉浸式的体验。
在《宝岛一村》中,他则让“眷村文化”成为连接两岸的纽带。来自大陆不同省份的眷村人,保留着各自的家乡口音、饮食习惯。这些细节不仅是对“眷村文化”的记录,更是对中华文化根脉和多样性的探寻。“从2008年到现在,《宝岛一村》已经巡演了340多场,去到过很多国家和地区,很多不同地方、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给我的反馈都是能够从中找到共鸣点。”这种情感共鸣,正是赖声川创作的动力——用戏剧打破地域的隔阂,让中华文化的“根”连接起每一个华人。

赖声川接受四川在线记者采访
在探寻文化根脉、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赖声川直言:“拥抱创新也很重要,但并不是为了追求新而新,因为重要的是好或不好,强烈或不强烈,以及传达的意念清楚或不清楚,这才是重点。”在近年来的创作中,他开始尝试将科技与戏剧结合,但他强调“科技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主题”。在《曾经如是》中,他运用了3D投影技术,让舞台上出现雪山、森林的虚拟场景,在投影和灯光变幻中,观众所处场景从山村变到纽约时代广场,再转到雪山。
技术仅是创新的体现之一,赖声川戏剧创作的角度与聚焦点也在与时俱进,并和演员的表演融为一体。“我的另一部新作《那一年,我们下凡》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情节,比如下凡的神仙把手机误认作砚台等,也有很多对新的现象与问题的探讨。”赖声川在访谈中透露,天马行空的想法很多也是来自日常生活,从这一层面来说,创新也可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如今,71岁的赖声川,依旧步履不停。那些从生活里长出的故事,那些扎根文化根脉的表达,早已超越舞台的边界,成为华语世界共同的情感记忆。他种下的不只是戏剧的种子,更是文化传承的火种——让华人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根,让世界在舞台上读懂东方的魂。这份坚守与创新,恰似一盏长明灯,照亮着中国戏剧的未来,也让文化的薪火,在代代相传中永远滚烫。
对话
在传承与对话中激活戏剧生命力
戏剧之韵
以方寸舞台,记录时代与共通情感
记者:戏剧的魅力是什么?在当下国家大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您认为戏剧艺术可以承担哪些独特而重要的使命?
赖声川:戏剧(表演)是人类最古老的活动之一。我觉得现在有两种演出,一种演出就是让你去忘掉,笑一笑然后忘掉生活的辛苦。另一种就是让你记得,记得一些我们可能会遗忘但是却重要的事情。
现在很多人习惯用手机获取碎片化信息,30秒不满意就划走,很难有深度共鸣。但进剧场的观众不一样,他们对人生有更深的要求,而戏剧的义务就是满足这种要求——不是给廉价的快乐,而是给营养,让观众记得那些被遗忘的人和事,记得人类共通的情感,记得我们是谁、从哪里来。
比如《宝岛一村》在台北首演,1500个座位座无虚席,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拄着拐杖来,看完说“这就是我们的故事”。现在眷村的房子拆得差不多了,但《宝岛一村》还在演,它成了一种“活的记忆”。未来人们想了解那段历史的情感温度,可能要看这部戏,而不只是看史料——因为戏剧是用情感记录时代,这种记录比单纯的事实罗列更深刻。
记者:您曾说“西方戏剧知识是方法,东方文化是内核”,具体到创作中,您是如何用西方方法传承中华文化的?
赖声川:并不是说西方戏剧艺术没有内核,只是很分散,没有成体系。而东方的则是整体的,或者可以说是一套完整的宇宙观。西方的方法确实可资借鉴,包括在结构、技术和表达逻辑上,如何让故事更紧凑、如何与观众建立现代对话。
比如我创作的《如梦之梦》,8小时的篇幅、环形舞台的设计,借鉴了西方现代剧场的理念,但故事里“轮回”“因果”的思想是很东方的。再比如,用写实主义手法串联25家人的150个故事,最终浓缩成三家人命运的《宝岛一村》,眷村人在困苦中互相扶持,哪怕一辈子回不了家,也把日子过出了滋味,这种“坚韧”“重情”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以戏剧手法把它呈现出来,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从中找到共情点。
创作之心
以作品说话,最重要的是讲好故事
记者:您从事戏剧创作40余年,持续创新的内在动力是什么?面对不同时代背景和观众审美变迁,您如何保持作品的先锋性与时代感?
赖声川:观众和媒体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什么新东西呢?我常常就想说,我们的压力好大,我们的创新还不够。但我常常又在想,如果你今天晚上让我选择,去看一个很新的东西,还是去看一个超好的东西,我是肯定选择那个好的。所以,我也不怕评论家跟我说,“这个作品写得太不先锋”。我觉得先锋不先锋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好或不好,强烈或不强烈,以及传达的意念和情感清不清楚,这个才是重点。
其实,做新一点都不难,关键还要看能不能持续下去。比如,《暗恋桃花源》放到今天,对很多观众来讲仍然很新。再比如,《宝岛一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一出来就无所谓新不新,它整个表达性已经强烈到不关注新与不新的问题。
米开朗基罗曾说过:“塑像本来就在石头里,我只是把不需要的部分去掉。”创作的时候,我其实不会想那么多,因为灵感本身会交付一个形式,然后跟随灵感把它串起来,串到最漂亮的一种状态。
记者: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您如何看待新技术在戏剧中的应用?如何在运用新技术的同时,坚守戏剧现场性、人文关怀的核心价值?
赖声川:我是不排斥技术的,但同时很坚定地认为技术本身不可能创造出作品。戏剧艺术回归到一个作品,最重要的就是故事。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最简单的沟通,具备了这些元素,戏剧其实只需要一个空舞台就够了。
不可否认的是,有时技术确实可以实现一些我们想要的舞台效果,但技术发展有时也并未达到我所期待的。9月底,我新的作品《镜花水月》即将上演,我在创造舞台上《山海经》里面的一些神兽时,原本需要也期待最新的一些科技,但是跟团队反复沟通,也去全国各地找各种内行交流后,我发觉我以为技术可以达到的一些效果,其实还不能实现。
至于人工智能,去年在乌镇戏剧节上,有一个媒体朋友告诉我说,他尝试请AI编一个赖声川风格的作品,结果AI真的写出来了。然后,我问他你觉得AI写得怎么样,他说只有短短十几页,大概成不了一个戏。
我想说,AI进步当然是非常快的,或许也能取代某些事情。但是戏剧这个行业,我觉得AI很难去取代,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AI不见得能理解。
文化之秘
以戏剧生态,激活城市的文化基因
记者:在不同的地域,如何去发掘当地的文化密码?在推动戏剧与地域结合发展的过程中,又如何将独特元素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和艺术高度的戏剧内容?
赖声川: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有它或明显、或隐性的文化价值。就好比说在成都,最明显的文化就是大熊猫、变脸等,而这些显性的文化密码其实已经产业化了。但当你走在成都的路上,你还会发现很多隐性的文化价值,就包括小吃、建筑,以及更隐性的一种心态。大家说到成都的慢生活很安逸,这种悠游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文化密码。
那有人可能觉得,隐性的价值是抽象的,要怎么去发掘并呈现?但其实有很多实际的东西是可以从隐性的文化价值中提炼出来的,最关键的就是要去讲属于自己的故事。以戏剧为例,很多剧院都想不断地引进国内甚至国外的优秀作品,但同时也应该给本土的作品更多的空间和机会。
记者:从台北“表演工作坊”到上剧场,再到乌镇戏剧节、江西会昌戏剧小镇,您一直在打造戏剧文化的生态圈。您觉得戏剧节、戏剧小镇这种形式,怎么才能真正“活化”一个地方?
赖声川:这些年大家总说“文化创意产业”,而在这6个字中,很多人会最关注“产业”,讲得再俗气一点,就是产值。但文化和创意怎么能用钱来衡量呢?全世界最珍贵的艺术品,本身可能没什么物质价值,但对人类的精神来说是无价的。
所以,我更愿意说“文化创意生态”,而不是“产业”。生态就像土壤,要有足够的养分、矿物质,才能长出东西;文化生态就是让一个地方的文化基因活起来,创意和产业是自然生长的结果,不是刻意追求的目标。
比如乌镇,它本身就是个“天然剧场”——小桥流水、老房子、石板路,都是戏剧的一部分。现在很多人说“乌镇戏剧节成功”,成功的核心不是票房秒杀,而是它给人的精神滋养。每年有很多人会请11天假,专门来乌镇看戏、聊天,觉得“这一年的精神需求满足了”。我认为乌镇戏剧节能够成功的核心原因之一,就在于艺术家自己在做最主要的事情,而我们想要做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来就不是在求那个数据,这种人与人、人与文化的联结,才是戏剧“活化”城市的关键。
底蕴之厚
以本土故事,点亮四川戏剧的未来
记者:四川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您觉得四川戏剧发展有哪些独特基础?又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赖声川:四川的文化基础太好了,川剧就是瑰宝,但可惜现在大家提到川剧,往往只想到“变脸”,并把它当“特技表演”来推广。但其实川剧的深度远不止这些,比如川剧的唱腔、剧本、表演身段,里面有太多东方美学和四川本土的特色,都值得挖掘。
我这次来成都,感觉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文化自信——有好的剧场,有政府的支持,有观众的需求,这些都是优势。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原创。现在很多地方喜欢“引进”优秀作品,这没问题,但一个城市的文化生命力,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原创作品。四川有那么多故事,老茶馆的故事、府南河边的故事、年轻人在这座城市奋斗的故事,这些都可以变成戏剧。
另外,四川也有专业的戏剧院校,也有很多热爱戏剧的年轻人,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多鼓励原创,让他们去发现自己身边的故事,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现在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独特的故事”太少了,或者说他们没意识到自己身边有故事。我建议每个年轻人都去问问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自己家里的历史开始了解,这里面就已经藏着太多戏剧素材了。
此外,不要怕“小”——不一定非要做“大制作”“大剧场”,小剧场、小作品也可以很有力量。比如我在江西会昌做戏剧小镇,成立了“会剧团”,演员都是当地年轻人,演的是会昌的故事,在小剧场演出,很受当地人欢迎。四川的戏剧人也可以从“小”做起,去把本土的故事变成剧,哪怕是小剧场演出,也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故事里有“四川的味道”,是外人写不出来的。
记者:您或您的团队未来是否有兴趣或计划与四川在戏剧创作、人才培养、戏剧节、活动策划等方面进行更深度的合作?
赖声川:我和四川其实有很多缘分,并且在作品和项目中也与四川有联系。在上剧场和会昌戏剧小镇,有很多年轻的演员,其中有一些也是来自四川。具体到未来的合作,我觉得还是讲求缘分。如果有机会,我愿意为四川的戏剧做一些事情,比如多带一些话剧来成都,多与这里的戏剧人交流,但最终四川的故事,还是要由四川人来讲,四川的戏剧,还是要由四川人来创作。只要四川的戏剧人坚守本土文化,挖掘本土故事,融入本土情感,就一定能做出有力量、有温度的作品,让四川戏剧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自己的声音。
记者手记
戏剧里寻找情与根
散场灯光渐次亮起时,剧场出口处飘来阵阵麦香,刚从《宝岛一村》故事里抽离的我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宝岛一村》从未缺席的道具——“朱妈同款”包子。
略微有些凉的包子下肚,攥着“99号”包子纸袋的掌心却微微发热。驻足剧场门口,看着散场的人群,采访赖老师时的对话在耳畔清晰起来,当时我问他“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戏剧创作”,他笑着说“人生总要做点什么去寻找答案”。彼时只觉得这是艺术大师的抽象感悟,可此刻,脸颊泪痕的余温还未散去,那句回答却在心里变得具体:或许他坚持的,就是用戏剧为每个人搭建寻找答案的舞台。
赖老师是一位温和、亲切、幽默的长者,采访中,他聊创作、聊文化、聊那些藏在故事里的东方智慧时,竟没有任何深奥难懂的阐述,就如同他的话剧作品一样,平凡但真诚,因而也充满力量。
在采访中,“情”与“根”是赖老师反复提及的关键词。赖老师口中的“情”,从来不是刻意煽情的桥段,而是《宝岛一村》里,朱妈揭开蒸笼盖时那若有似无的包子香;是《暗恋桃花源》中,江滨柳与云之凡隔着几十年岁月的那句“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在采访赖老师之前,我一直觉得相比书本、影视等艺术形式,戏剧是有门槛的,不仅因为其受众范围更小,也在于对观众的审美接受能力本身就有要求。但赖老师在戏剧中倾注的“情”,完全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
而“根”,则是他作品里从未缺席的文化底色。赖老师始终坚信,一个人对“根”的认知,往往是从了解自己的家开始的,也正是对家庭温情的珍视,对文化根脉的守护,让他的戏剧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个人与集体的精神纽带。
当71岁的赖声川在掌声与欢呼声中带领演员鞠躬谢幕时,这份坚守的意义愈发清晰。40余年的创作生涯,从来不是追求 “大师” 的光环,而是始终以戏剧为桥,让漂泊的情感找到安放的港湾,让断裂的记忆重新连接成链。在这些故事里,每个人都能读懂自己的情之所系,找到自己的根之所在——这便是戏剧最深厚的力量。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九十四期
执行:杨昕
记者:田珊
摄影:吴枫
剪辑:李蕾 郭雨荷
海报:刘津余
编辑:杜馥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