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凸凹
感觉冬天还未到,就要过去了。去年也这样,一个冬天下来,羽绒服没穿,毛衣也少着。四季分明的万古成都,怎么就成了暖冬,成了昨天开冷气、今儿启热风,模糊了季候边界感的地方?
看来不光人心有变数,物事有变数,推而广之,延宕开来,万事万物也有变数。
这就对了,“万变不离其宗”的指归,正是变才是恒久的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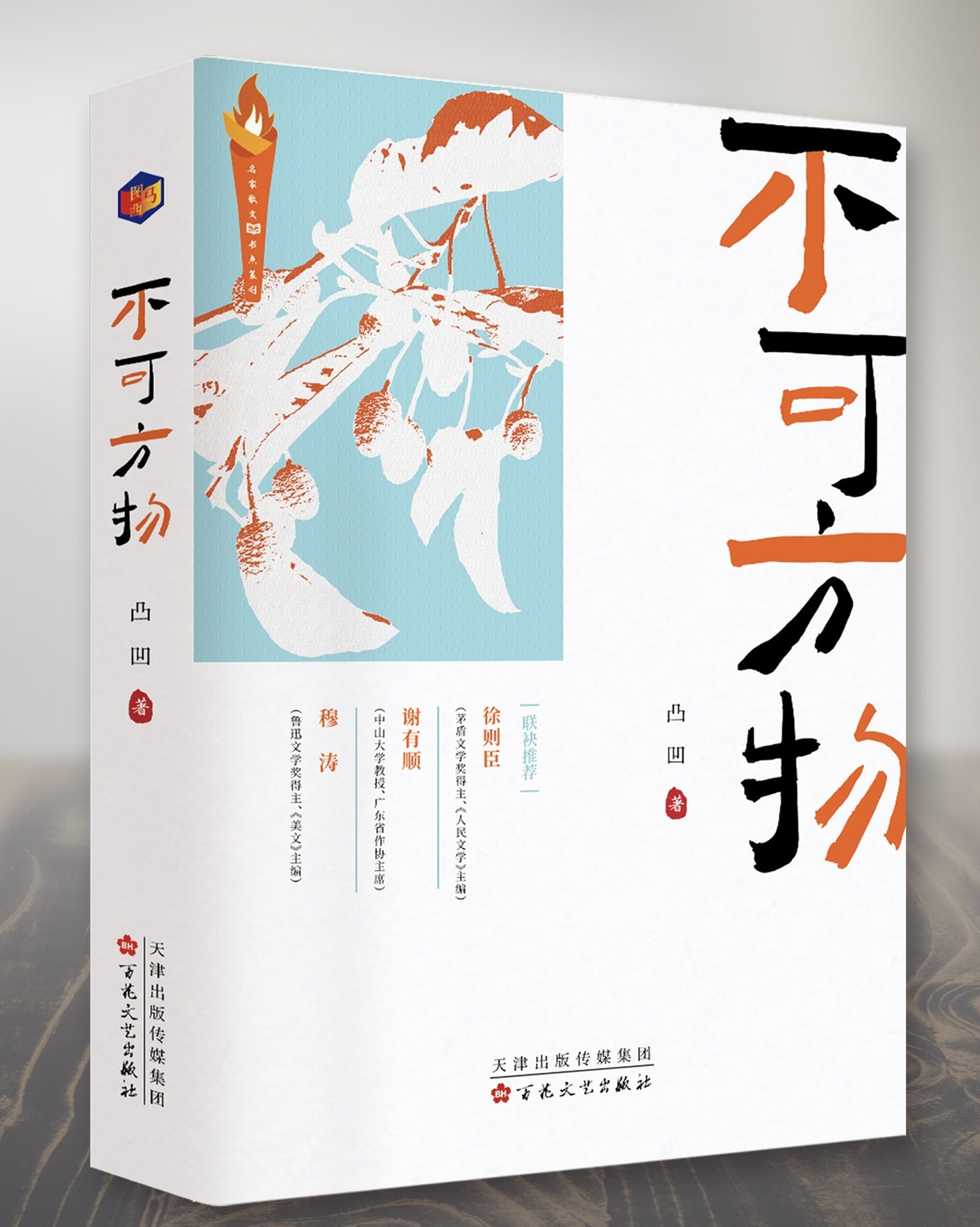
创作也在变。不知不觉,竟写了散文。之前,主要写诗,大约从2011年开始,又新起了小说的灶。自此,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剧本、歌词等同时操持,成了“吃得杂”的码字工。
码了字,又有了将字变成书的机会,自是好事。这样一来,30多年间,就出了点书,其中的几本是散文。
因为远没达到可以肆无忌惮、随心所欲码字,更没实现出书自由,所以,面世的几本散文,均有一个由题材框定的主题。《花蕊中的古驿》(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年11月)写的是龙泉驿,《纹道》(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写的是“蜀锦·蜀绣·漆艺——流光溢彩的国家技艺”,《民族花灿》(成都时代出版社,2009年7月)写的是四川的少数民族;与儿子魏亦合著的《首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写的是“成都东大街浮世绘”;与文友合著的《天下客家》(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10月)写的是客家;《锦江商脉》(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写的却是以成都市锦江区为主体的岷沱二江流域的古今商业。
回过头看,从2004年到2011年,7年6本。这样由字变书的体量,大得让我吃惊、汗颜。跟着,就生出一个小小的奢望,愿有个机会,出一册散文。不一定厚,薄薄的一册就好。不是说7年出的6本不是散文,它们当然是了,但是文学谱系内的非虚构。
在我的认知里,小说是虚构的叙事,散文是真实的呈现,诗歌则是半虚半实的艺术。6本是散文,但它们又是有限定词的散文:人文地理散文。不是说人文地理散文不好——我的已进入出版流程的《蜀中记》和《龙泉山传》(上下册)也是人文地理散文——只因它们已然成书,不是一两本,而是好几本了。因这个道理,就想出一本纯粹的散文——没有设定、无法归类、道说世间万物生命的有常和无常的文字。
何谓散文?我在《向内的非虚构与时间的隐秘地——读赵晓梦散文集〈缓冲地带〉》(《中华读书报》2024年11月27日)一文中,谈了一点浅见:
有一种广义的说法为,文学式样中,散落在小说、诗歌地盘之外的所有文字,皆为散文。关于散文的界定、定义,各有各的阐论,我想说的是,即便是从广义的判定出发,散文也是不应与小说搭界的,换言之,不该与虚构艺术挂钩。所以,在我这里,“非虚构散文”这一标签不存在,因为与之对应的“虚构小说”不存在,虽然写虚构散文的人并不鲜见。“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记念刘和珍君》)借用大先生的语汇,以及大先生作为顶级散文作家的作为,我以为,操持文学这门手艺的人,只有写散文且写出好散文的人,方可称为作家中的“真的猛士”。如此说,理由有三:
首先,写散文需要作者站在文字中,望着读者的眼睛现身说法,目光稍有躲闪就是心虚、示怯。小说中的作者躲在背后,不需要出来站台,诗歌则是可有可无、亦真亦幻。这个,有点像开金店的老板,一些敢于将自己的名姓堂堂正正亮于店招,一些则不敢。
其次,写散文需要作者诚实、坦荡,字字有来源,句句有依凭,一句话,做到巴金先生宣示的四字:“要讲真话。”一些作家,甚至个别著名作家,写小说、诗歌没问题,散文也可以写,只要不涉及自己的身体真相和内心真相,即不涉及自己的生平、行迹、脾性、嗜好、生活以及思想锐度、内心活动,都可以写。他们的举动,我理解,正如理解那些不愿公布自己的真名、性别、年龄、住址、电话等“隐私”的网友。不理解的是,倘散文中没有建立在作者真身之上的作者的态度、立场,拿什么让人信服?假话、套话、大话不仅压不住事实,带不出心跳和温度,还一定会在时间的洗涤术中被反噬。小说也讲真实,那是指虚构出来的艺术的真实,譬如莫言,为了这种真实,甚至直接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诗歌也讲诚实,譬如其中一种诚实是将实的写虚、虚的写实。
再者,散文需要作者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作者如果没有广博的阅读、丰饶的阅历,面对疑难问题、敏感场域,是引不出有价值的话题的,更拿不出让读者顿悟、惊喜、大有收获的真知灼见。一篇散文或高明或平庸,只要一开笔,就亮了底牌,内里是否有见筋见骨、见血见肉的洞见,一目了然。如此的高门槛与严苛要求,自然让胸无点墨的心虚者望而却步了。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散文,也是我努力设定的戒律和追求的彩虹为我打出的实样。在练习的路上,我写过一些练习的文字,像牛像羊,零零散散放牧于一些报刊,我想把它们收回来,变成书的样子。
在我还没想好怎么变时,机会来了。“魏老师有散文没?我们免费给您出。”一位跟我从未见面、素无交集的人,在微信上留了言。那天,是2024年9月12日。
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路,选了20多篇稿子,打捆成《不可方物》,动作跟割麦后挽结成一把没什么两样。
按照多年的愿景,这些稿子,大致都属写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生命与命运的纯散文。写人物的,不是个我,就是他者——李冰、杨升庵、艾芜、崔世远等;写动物的,有兔、狗、牛、蜂、鼯和鹡鸰;写植物的,有茶、桤木和猕猴桃。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卷三“物非物”呈现的生命本相与运程,却是书籍、隧道、月亮和雪山的。
多有写动植物,除了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倾心博物学和名物学这种堂而皇之的说辞,我想,还有两个底因:植物的背后,是家父家母的工作单位:万源县茶果站;动物的背后,是我小时候常去的与重庆动物园仅咫尺之隔的爷爷奶奶家。
收入集子中的作品,最早的一篇《中学之初》写于1999年1月,最晚的一篇《会飞的茶》写于2022年10月。
从1999年到2022年,说了半天,什么都是物,只有时间不是。说了半天,什么都不是物,只有时间才是——只有时间才能不可方物。
没错,最硬的物,是时间。一万头最犟的牛,也犟不过一秒钟的内核与走向。时间就是时间,自己不变,只让非自己变。
所以的所以是,让时间带着《不可方物》走吧,宇宙茫茫,走到哪黑,就在哪歇。
写这个后记的时候,DeepSeek正像恐龙一般突如其来,风卷残云,大有改写世界之势。有人欣喜若狂,有人如临大敌,有人默不作声。
见“AI热”霸屏,忍不住,也在朋友圈来了一嘴:“晨起,感想一枚:AI智能化人脑化的不断升级,将给诗词歌赋、虚构艺术和说理性作品带来巨大压力,而作者亲历的、有个性有价值的非虚构作品,或有路可走。”在公共资源——古今中外的公共信息和公共情感——里抢食,一己的脑花花,哪能跟亿万万台智能机器的算力较力?
果如此,一不小心,《不可方物》有幸了——或许尚存一线窄路偏径可走。
(《不可方物》,凸凹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