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庞惊涛
夏钦的《杜甫:迈向诗圣之路》有不少新意,在既有杜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跳出传统诗史、忧国忧民的叙事路径,从杜甫的人生轨迹、情感维度、创作细节等多方面提出一些新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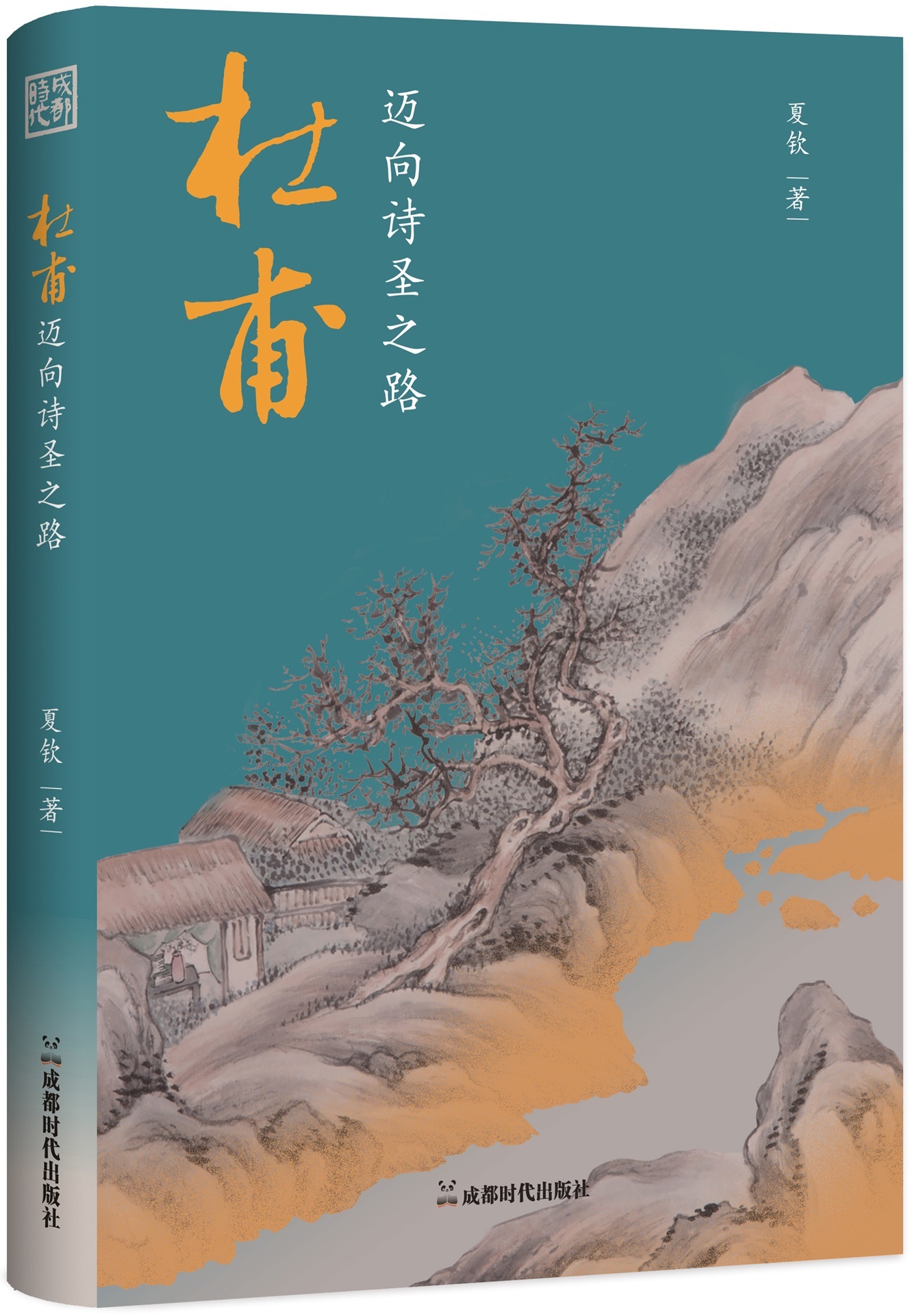
一是摒弃杜甫全景式的生平叙事,截取“诗圣进阶”的关键生命周期,以成就“迈向诗圣之路”的核心命题。
过往研究多将杜甫诗圣地位的形成归因于安史之乱中的“三吏三别”等史诗式诗作,或笼统提及蜀地生活对其创作的影响。本书首次将杜甫辞官后漂泊大西南的11年(759—770年)视为其“迈向诗圣”的核心转型期,通过文本细析与历史语境还原,尤其是数据分析,得出杜甫生命及其诗歌写作的关键周期的结论。
根据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杜甫这11年的创作,占现存杜诗的70%以上,涵盖日常书写、自我解构、悲悯升华3个关键维度,是其诗歌题材从社会纪实拓展到生命体验的关键时期。这样的数据分析和诗歌题材分析,对更好地理解诗圣这个文学史概念,确有一定贡献。
对成都草堂的价值确认,也可看出作者不蹈故常的努力。在作者看来,成都草堂不单纯是杜甫的避乱居所,更是杜甫“理想生活的桃花源与精神寄托的乌托邦”。
二是分析杜甫的朋友圈数据与人情网络,还原杜甫的立体社交人格。
本书使用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以更精准详细的视角,从李白、高适等诗友,严武、韦济等资助人的视角外,以数据化与场景化相结合的方式,搜罗和亮化了一个崭新的杜甫人情网络视点。
根据本书统计,在杜甫现存的1458首诗中,交游诗747首,涉及402人,平均每友近两首。按类型分,又有物质资助型(如严武30首赠诗、章彝13首赠诗)、精神共鸣型(如郑虔13首赠诗、李白13首赠诗)、方外之交型(如赞公和尚、旻上人)等类交往。这种分类法,打破了杜甫社交仅为“干谒求仕”的片面认知,很有开创性价值。
书中重点还原了几位被忽视的关键人物。如杜甫辞官后投奔的秦州族侄杜佐、同谷县宰,他们虽未提供实质帮助,却成为其乱世人情观察的样本;又如为杜甫编首部诗集《杜工部小集》的樊晃、写《墓系铭》的元稹,本书将二人定位为“杜甫‘身后名’的‘第一推手’”,补充了杜诗从小众流传到经典化传播的关键链条。
三是发现杜甫幽默与自嘲的崭新人格,改变其悲情诗人的固化认知。
这种创新集中体现在情感、气韵和理路都臻为圆熟上乘的《代序:诗卷长留天地间》一文中。作者对过往杜甫研究中强调“穷年忧黎元”的愁苦形象,以及“杜甫没有青年,李白没有暮年”的刻板评价持怀疑态度,通过文本细读,挖掘出杜甫鲜为人知的幽默特质,突破了杜甫人格研究的单一性。
从《空囊》“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中,作者解读出杜甫“以‘留一钱’自嘲贫困,用夸张消解窘迫”的黑色幽默;从《课伐木》序“作诗示宗武诵(仆人)”中,还原“让幼子向不识字仆人读用典繁复的诗”的迂阔滑稽场景,证明其“并非全是‘醉里眉攒万国愁’,亦有文人式的诙谐”。就此,作者认为:“杜甫的幽默是‘苦难中的精神缓冲’。”这一发现,丰富了杜甫沉郁之外的人格层次。
四是聚焦日常题材开拓,定位杜甫诗歌革命的平民化转向。
过往杜甫诗歌艺术研究多将其归为现实主义深化,作者则从文学革命的角度,提出新的认识:明确杜甫是“唐代首个将‘鸡栅、装修、蔬菜、仆人’写入诗的诗人”。
为此,作者引用日本学者古川末喜《杜甫农业诗研究》,结合《催宗文树鸡栅》《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等诗,证明其“将‘乡野琐事’提升为‘诗歌主题’,打破‘唐诗以山水、边塞、宫廷为尊’的审美惯性”,指出这种日常书写暗含人道主义突破。
又如,诗中提及仆人杜安、阿段的名字,打破唐代诗人忽视奴仆的常态,凸显其超越时代的平等意识。这与电影《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对林邑奴的情深义重,都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
还有一个新意,是作者对杜甫与城市关系的现代性解构。本书从双向奔赴视角,重构杜甫与成都城市文化共生的关系。成都对杜甫的滋养,不仅是远离战乱的安全屏障,更以温润气候、丰饶物产、友善邻里激活其抒情能力。如《春夜喜雨》“润物细无声”是“成都雨景与诗人心境的共振”,《江畔独步寻花》是“成都市井生机对其创作的唤醒”。这些诗句成为“成都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文学符号”,成为诗人滋养成都的最好证明。
(《杜甫:迈向诗圣之路》,夏钦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