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在线记者 张斌 摄影 吴聃
当三星堆神秘的青铜面具与中原庄重的青铜器物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明火花?在9月27日举办的2025三星堆论坛上,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大伦带来了一场关于“商蜀青铜文明比较”的深度对谈,从时间、空间、技术、文化四重维度,为我们揭开了两种文明既关联又迥异的发展图景。

高大伦
“认识一个文明,不能只看它有什么,更要看它在同时代文明中处于什么位置。”高大伦开宗明义地指出,青铜器作为判定文明成熟度的重要标志,是观察三星堆与中原关系的一把钥匙。
高大伦介绍,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约夏中期)已出现青铜容器,标志着中原青铜文明步入成熟阶段。而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晚期,如三号坑约为公元前1100年至前1000年。“从青铜容器的出现时间看,中原文明更早成熟,三星堆则展现出一种‘后来者’的跨越式发展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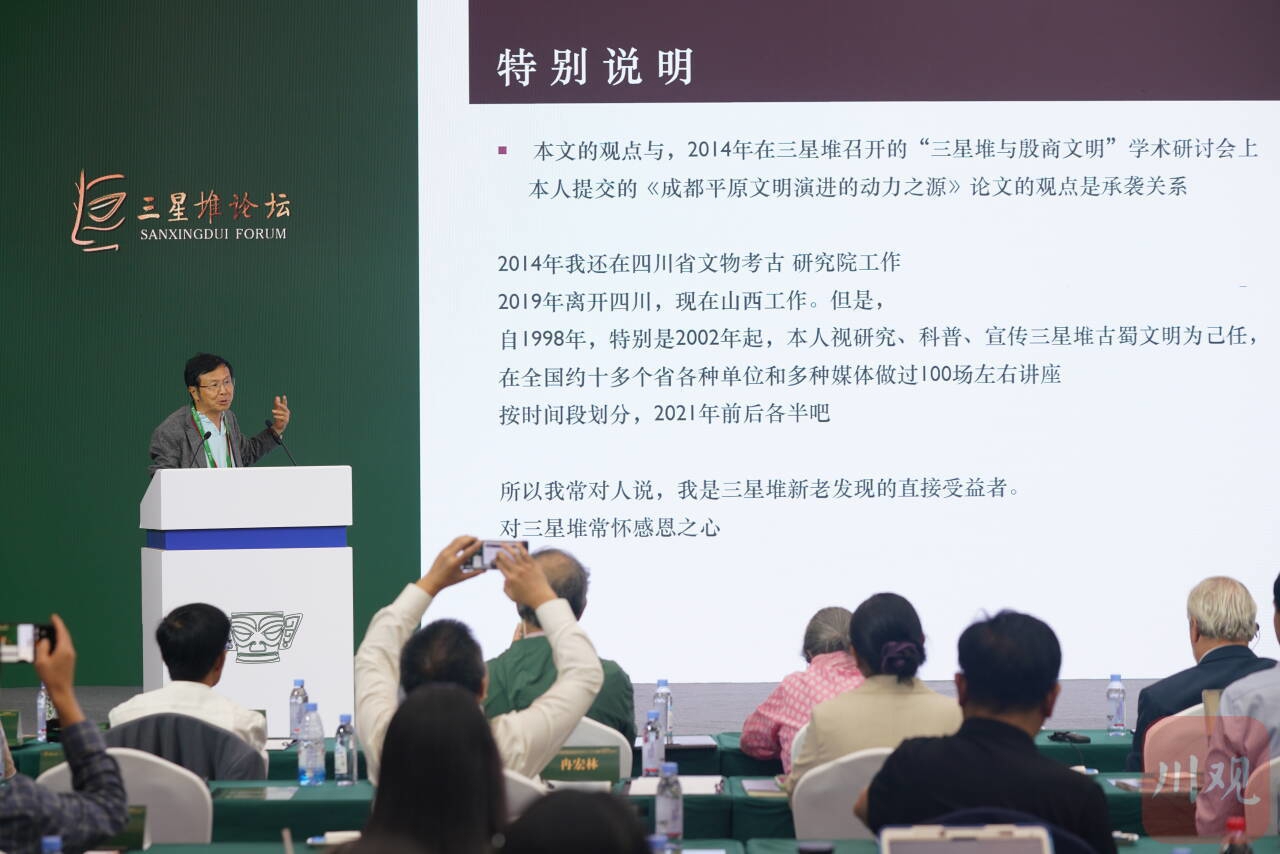
高大伦
从出土范围看,商文明的影响极为广泛,青铜器出土数量高达6万至7万件,遍布河南、河北、山东等十多个省市。而蜀地文明则高度集中于约8000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出土青铜器约2000至3000件。
在技术上,商代已形成“采—炼—铸”一体的产业体系,范铸法、分铸法等工艺成熟规范,青铜器风格凝重、精致、精工。而三星堆青铜器则在吸收中原技术的基础上,展现出强烈的本地化创新。“他们甚至会用一些‘取巧’的办法,比如巧妙拼接、组合铸造,来解决大型复杂器物的成型问题。”高大伦特别指出,三星堆工匠更注重造型的表达自由与神秘气质,其神树、人像、面具等器物,堪称“青铜造型艺术的最高峰”。
最根本的差异体现在文化内核上。商文明通过青铜礼器、文字铭文、族徽等构建起一套严密的礼制与身份系统,而古蜀地区迄今只发现一件铸铭青铜器。三星堆青铜器多为神坛、神像、祭祀用具,体现出强烈的“神巫”色彩。“中原重‘礼’,蜀地崇‘巫’。”高大伦表示,“这种精神世界的差异,可能直接塑造了二者不同的器物表达体系。”
高大伦强调,比较并非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三星堆并非“外来文明”,而是在与中原持续交流中,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并大胆融合创新的结果。“它用中原的技术,表达古蜀的灵魂;用四方的资源,成就自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