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潋
2024年4月,吕宾的诗集《我用阳光洗手》出版,2025年7月再版。我认为这是自然的事,反而使我思考其诗歌语言的表达似乎失去了辞格,如在古墙上掉落一枚词语,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自然地弹奏,无须平平仄仄,就可以让我们朗读多年。这是吕宾在40年前与我们讨论的话题:技巧在于“无为而为”。他以40年的阳光手帕,擦去泥土,即为纯洁的——诗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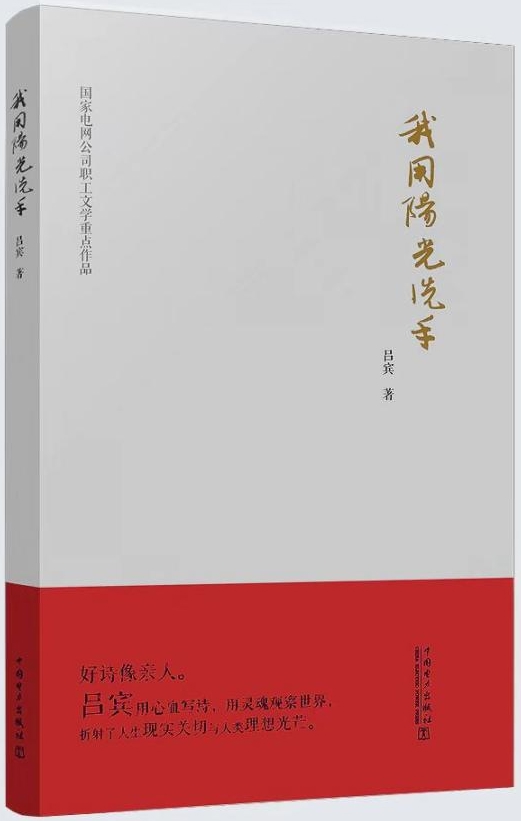
以“我用阳光洗手”为诗集名,如小孩用清凉水洗手巾一样骄傲和幸福。以“洗手”这样一个个体的行为动作作为隐喻或象征,表达在复杂的生活环境里的自我净化,或一种精神的觉醒,如“谢天。我来了/谢地。我不作声/诗歌是我最后的亲人”(《谢天谢地》)。
吕宾的诗歌语言很夸张,读起来几乎不能“呼吸”,但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实景与虚景”。“拉开一株树与另一株树的距离”“你伸出月光一样的手 拨亮每个方块字/和凸凸凹凹的比喻/我惊愕了”(《未认识的开阔地》);“无名峰”在他的笔下,也就是一枚“大盆地吐出来的拳头”,这样的想象和夸张,似乎让人“窒息”。
即使是《我享受春天》,“我以一头老牛的目光看着这些嫩草/我感到我的周身长满了嘴唇/春。春天啊”。把俗语“老牛吃嫩草”分开读下来,心里的气流很难顺下去,还“周身长满了嘴唇”,似乎在胸腔里梗着。在他的季节里,也是“一个埋雷的季节”(《这是一个埋雷的季节》)。这些意象构成新的虚像,诗味有陡然的况味,不可描绘。
吕宾诗歌的意象很多是错位的语言表达,很难疏通诗歌语言的流向。其实,他的诗歌朴实、简单,不晦涩难懂,而是把意象设置在“语言的错层”里,读者一时不会“咽下去”而已。
“错层的语言”有的在一个句子里,有的是在前后的语句中,甚至在诗题与诗句的空间里,似乎是在照应。
如《我在枝头等你》的“请举起最初的一片叶子聆听我/春天我没有语言/许多话都被花四面八方说了/所有的日子朝着一个方向/滚动”。“举起”与“叶子”应该没有错搭的问题,“聆听我”与“叶子”就没有直接关联了,“话”“花”与“说”也如此;“所有的日子朝着一个方向”也是如此,而“所有的日子朝着一个方向/滚动”的“滚动”,就让人更“不可理喻”了。
这就是吕宾诗歌里的意象,以错位的语言搭配构成其本意。一个独立的词语,就创造出一个新的语感。
还有,吕宾把诗歌语言揉碎,再把碎片化的语言粘连起来,构成一个新的语意流向。“分开甜蜜/才知道那一片绿叶是衣裳/那一朵花开是嫁妆”(《我们的水果充满阳光》),“甜蜜”是一个非具象名词,吕宾把它具象化,于是才会“分开”,后面两个句子的语意才会符合语言表达的逻辑。在诗集里,这样的语句还有很多。
因个体生命的体验差异,使我们不得不以哲理性思考吕宾的诗歌本客体倒位的语言问题,即诗歌语言被撕裂后,重新组合为新的语言符号。
《黑的灯》是吕宾在1987年秋天构想的。“黑暗也是一盏灯”,这源于“黎明前的黑暗”,他把语意倒置后构成新的具象(意象),就具有新的语境。如开头两句“在阳光泛滥成灾的地方/黑暗也是一盏灯”,还有“转过身来向后走/也许也是一种前进”,其间有“头辈子睁眼睛死去/这辈子闭眼睛活人”“到处能听到动物的声音/山是鸟儿的语言/水是鱼的共鸣”。这是个体生命体验转化为诗,以诗味与哲思共鸣。
吕宾为诗40多年。在诗集后记中,他写道:“诗是醒着的;以诗养心,以业养身;诗歌是人类的绝对的精神,是切入世界的伤口,诗人是人类最后的良心。诗歌……也是我的信仰。”
我以为然。在与语言的较量中,吕宾对诗歌作出了贡献。
(《我用阳光洗手》,吕宾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25年7月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