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凸凹
当客家属性与小说生成机制相遇,李顺治的长篇小说“大河三部曲”压卷之作《大河奔涌》出现。作者将故事原型地定位在蜀西省益都市青江区的客家聚落东山镇,将一众人物大多设置为客家人,还将客家的诸多民俗活动植入故事中。可见,该作品是诞生在川西地区的首部纯粹的客家题材长篇小说,是说得过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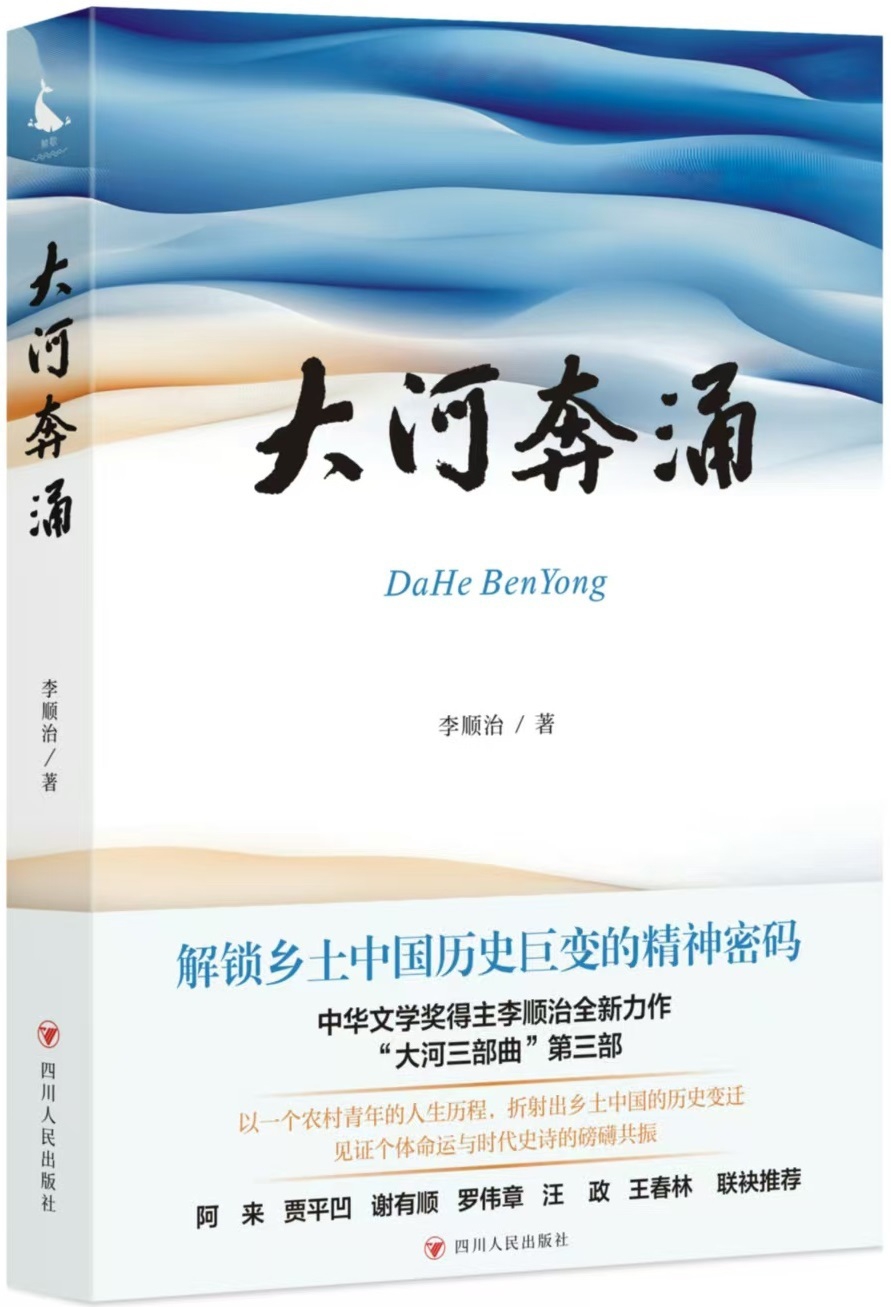
通读细品《大河奔涌》,我发现,客家的诸多属性,可以在小说的创生机制里找到自己身体里暗涌的大河。换言之,作者在自觉不自觉中,将客家、小说和作品中奔涌的毗河这3条大河拥在了一起,用新的生命开解过去的死亡,“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博尔赫斯《另一次死亡》)
用迁徙实现反转
在小说的生成机制中,为得到好看、引人入胜、欲罢不能诸效果,往往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硬核引擎,驱动故事、带着读者一步一步往前走,直至没有终点的终点。这个手艺,对应在现实生活中,是现如今那些一浪高过一浪的爆火得上热搜的新闻存态——它们总是在不断的剧情反转中博得大流量。
从客家缘起来看,迁徙是客家最耀眼夺目的文化符号。经五六次迁徙于宋代达闽粤赣后,又在闽粤赣之间反复迁徙。后因当地人多地少且政策苛刻,遂一分为三:一部分留闽粤赣,一部分漂海外,一部分迁巴蜀。迁至巴蜀后,又经反复择址迁徙,其中一支最终落担成都东山,成为东山客家。他们插占土地,辛勤耕耘,繁衍发家。甚至还有少数客家人再度迁徙——如小说中曾家寨子的一支后人迁去了贵阳。一次次迁徙,一次次变迁,一次次反转。在厄运中迁徙,在反转中改命。
小说剧情从主角廖长江考上重点高中青江区大弯中学的喜讯开笔。廖长江因穷怕交不起学资让家里难堪而选择保密,结果密没保到,最终还是去了。去有两条路,正常走大路,为抄近道走山路,这一走有了“高山之巅”给予的人生大格局的感怀,顺便还救了同学徐三娃的命。
在学校,廖长江爱上女同学曾霞,以为对方也爱他,就写信表白,结果碰了钉子,于是决心以高考表现俘获芳心。哪知高考因突发疾病失败(后来得知,曾霞已与同学吴凯双双考上复旦大学并成为恋人)。
都以为他会隔年再考,哪知他为家里省学费,去当兵以期上军校,跟着又参加维和部队去了非洲马里。回国后,因为立功表现,升了职,有了实现读军校的初愿。面对美好前程,他竟然坚决要求转业,原因只为一个承诺——为在维和中牺牲的光坡村战友廖长东尽孝。
此后的反转剧情,就只在青江区的空间内,在廖长江的人生大世界、生命大舞台迁徙并展开。
我在这样的反转中追剧,直到剧终——廖长江与曾霞走进婚姻殿堂的同时,一个贫困山村被反转成幸福美村。然后掩卷,倒片,徐徐回放。
用反转开辟正道
有什么样的方向,就有什么样的目标——目标昭示方向,但并不给出方向的具体路径。所以,事物的正确运行轨迹,往往是一次次迁徙反转,一次次扭转危局,扳正方向,并无限趋近理想的康庄大道。
这样的轨迹,既是小说故事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创作矿脉,也是客家人用迁徙实现反转,用反转开辟正道的理性纠偏与逐浪前行。
当廖长江将自己的事业与追求落子在东山一个贫困山村后,他连同村子的迁徙向径与图腾,就成了就地起立的向上拔节——用富庶和幸福的云上高度标示迁徙的长度。而这,正是客家人的拿手好戏。客家人总能把一块陌生而荒凉的所在,耕读成一方风生水起的家园,并生长出一众大名鼎鼎的人物。
有过多地多岗历练的廖长江,在对东山镇自然地理、人文历史进行深入调研、缜密思考,以及带领村民代表到江浙先进村参观考察后,为村子的未来迁徙路描绘并决心开辟出一条“正道”。
小说家开辟正道的能力得益于小说家的小说能力。客家人开辟正道的能力得益于客家人与生俱来的耕读传家、诗书传家、尊师重教的教养和勇于开拓、放眼天下的视域。
用正道撑开命局
小说是用“小”——小的细节、小的物事、小的波澜、小的心跳等——去实现大,用大去增寿续命,以此完成作品走得比作者远,比时代远的使命。字喊出词,词喊出意,意喊出一片不二锦绣。优秀的小说家能够做到将一把散沙撒成沙金,然后用强大的气场罩住,又用一道神光收回,最终铸成万古金字塔——作者和作品的命局自此被撑开。
客家人个子小,地盘小,四处迁徙,蛰身边邦,却能逆袭命运,异军突起,收获令人瞩目的辉煌。究其里因,恰是他们修谱立祠,崇尚祖先,以举族迁徙、聚族而居、重情重义、抱团取暖为习积淀的结果。
回到《大河奔涌》。我们看见廖长江在自己绘制的“正道”上遇山凿洞、逢水搭桥,大踏步前进。面对建设、治污、招商、营销等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修路筹资、拆迁、招标、踩葱、采石场斗殴风波、“铁算盘”等层出不穷的拦路虎和疑难杂症,他和他的团队更是神挡杀神,鬼挡杀鬼。
廖长江成功了。而成功,正是一波三折、不断反转的结果:“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奇怪,当你越满怀期待想要办成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越不容易办成,‘成功’像是故意在躲避;当你不再期待的时候,这件事情会自己送上门来,给你一个‘成功’的惊喜。”
或许读者看到的是廖长江的创造能力、热血理想和英雄主义的急智彰显,而我看见的却是廖长江背后那个须臾不离的身影——作者李顺治的身影——在不停地敲键盘。
《大河奔涌》刻画细,环境氛围、情与景渲染到位,对生活有见解,对事业有思考,解决问题有路径有办法——我以为,这一切,得益于作者的人生经历、阅读思考和对事物运行本质的全面观察与深入体验。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是开不好、写不出“周末板凳会”以及做好会后的个别交流,也解决不了电表问题。于是,“周末板凳会”完善了,“光坡大讲堂”开讲了。
再一个,我感觉作为虚构艺术的《大河奔涌》有一半甚至一大半具有非虚构性质。若作者肚里没有货,是不敢如此直视、正叙的,只能虚晃一枪、剑走偏锋、瞒天过海,在全能视角的旗帜下,无限夸大地写成他者的内心世界,把作品弄得云里雾里,貌似深沉厚重,不同凡响,而该书人物的内心世界、人性纠葛、性格脾气,却被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以人物的外化言语与身体行为作出由外向内的客观表达。如此的舞台化表达路径以及对核心人物的浓墨重彩凸显,让这部小说又多了一个走向,即转化影视的可能。
小说终究是写人和人的命运的艺术。合上书页的一刻,一个阳光、正直、精力充沛、能力超强,生命不息奋斗不休的当代客家人形象跳了出来,他叫廖长江。
(《大河奔涌》,李顺治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