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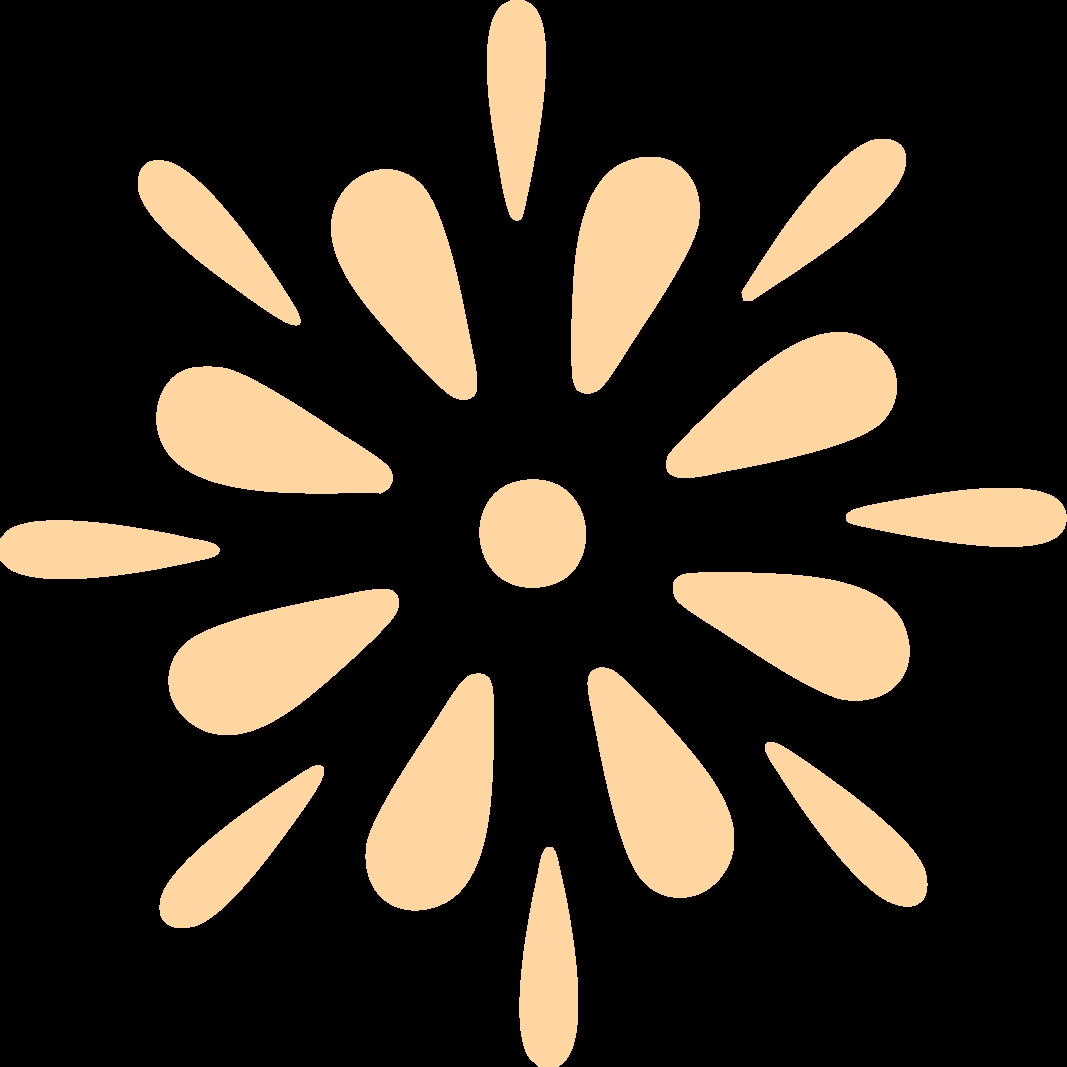
编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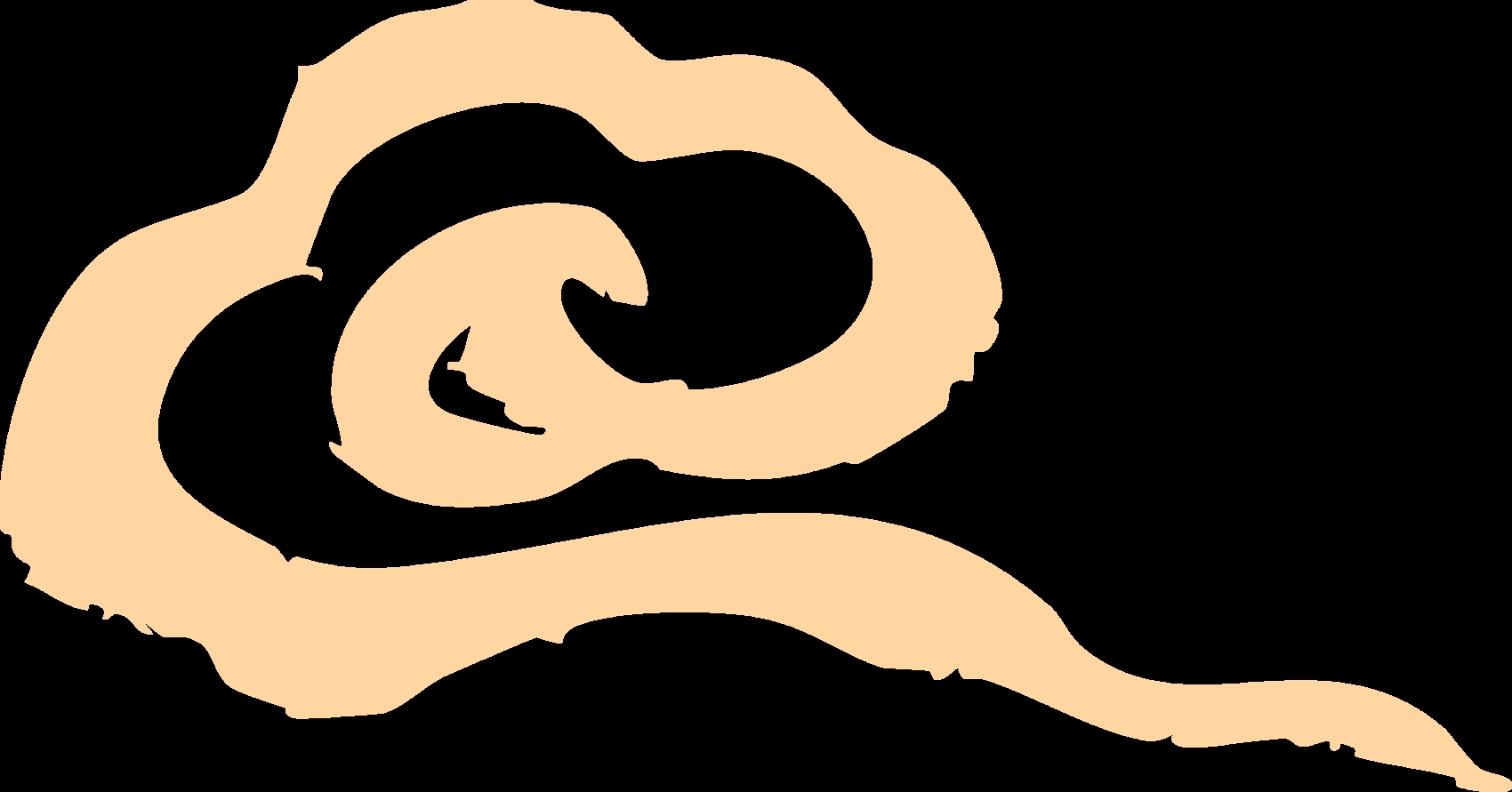
刘海琨
舞蹈《阿妈就是那座山》以四川凉山彝乡的人文风貌为底色,以意蕴悠长的肢体语言刻画母亲的如山风骨,谱写彝乡母爱的史诗。
民族文化的具象化表达
舞蹈作为一门身体艺术,其核心魅力在于通过肢体动作、道具运用与空间调度,构建超越文字的表意系统。《阿妈就是那座山》将彝族文化中的核心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舞蹈语言,让每一个动作、每一件道具、每一处调度都成为叙事的组成部分,既保留了民族艺术的纯粹性,又实现了情感表达的穿透力。
在表现阿妈劳作场景时,舞蹈语言呈现出鲜明的生活质感。搓麻、织布、牧羊、守望等日常动作被艺术化加工,既保留了劳作的真实性,又赋予其舞蹈的韵律感。舞者们双手交叉往复,模拟搓麻的细腻动作;脚步轻移、腰身微拧,还原织布时的专注神情;手臂张开如鹰翼,再现牧羊时的意境。
这些动作没有复杂的技巧堆砌,却以发力方式与节奏控制,将阿妈日复一日的辛劳与坚韧具象化。尤其是中年阿妈扮演者的肢体表达,通过肩部的微颤、腰部的沉坠、脚步的蹒跚,刻画出岁月在母亲身上留下的痕迹,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生活的重量,让观众在熟悉的劳动场景中感受到母爱的深沉。
作品中群舞与独舞的交替,进一步丰富了肢体语言的表意层次。群舞时,舞者们以整齐划一的动作构建出群山连绵的景象,肢体的齐动如山体的起伏、风声的流动,营造出雄浑磅礴的气势;独舞时,中年阿妈的肢体动作更加细腻内敛,通过手指的蜷缩、眼神的凝望、身体的前倾,传递出对子女的牵挂与守候。
这样的肢体叙事,既展现了自然的伟力,又凸显了人的情感,让山的意象与母爱的主题相互交织,形成艺术张力。
彝乡意境的沉浸式营造
舞蹈的空间调度与视觉设计是构建作品意境的重要手段。《阿妈就是那座山》在舞台空间的运用上,既遵循传统舞蹈的叙事逻辑,又融入现代舞台艺术的表现手法,营造出沉浸式的彝乡意境。
舞台布景简洁而富有诗意,背景是淡淡的凉山剪影,远山如黛,云雾缭绕,配合暖黄色的灯光,将观众带入晨曦中的彝乡。
在灯光设计上,在表现劳作场景时,采用明亮的自然光色调,凸显生活的烟火气;在表现送别与守望场景时,灯光逐渐暗下,聚焦独舞的阿妈,营造出深沉内敛的情感氛围;在群舞展现群山壮阔时,灯光全面铺开,色彩转为暖红,如夕阳映照山峦,传递出温暖而厚重的情感。
在空间调度上,作品通过舞者的位置移动与队形变化,构建出空间层次。在群舞时,舞者们以圆形、弧形等队形排列,模拟群山环绕的形态,形成视觉冲击力;在独舞时,舞者多处于舞台中央或边缘,与群舞形成点与面的对比,突出个体情感的细腻表达。
例如,在表现阿妈守望子女归来的场景中,中年阿妈独自站在舞台右侧,身体微微前倾,眼神望向远方,其他舞者则以低姿态分布在舞台左侧,形成绵延的山形,既突出阿妈的孤独与坚守,又以群山的意象衬托出母爱的博大。
这种空间调度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视觉美感,更让情感表达与意境营造相得益彰,让观众在视觉沉浸中感受彝乡的人文风情与母爱力量。
母爱的多元意象与象征
《阿妈就是那座山》以母爱为题,却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歌颂母爱,而是扎根本土,从阿妈的日常生命经验出发,通过具象化的生活场景和细腻入微的肢体动作,让观众体会到母爱的醇厚绵长。
作品对母爱的刻画贯穿于阿妈生命的不同阶段:青年时的阿妈,眼神清澈,动作轻;中年时的阿妈,脊背微驼,动作沉稳,既要承担繁重的劳作,又要牵挂远行的子女,每一个眼神都饱含牵挂与不舍;老年时的阿妈,步履蹒跚,神情安详,在守望中沉淀下岁月的智慧与从容。
在彝乡的文化语境中,母爱还与大山的意象深度绑定。阿妈如大山般沉默而坚韧,用一生的辛劳守护着家庭与子女,正如大山用宽厚的臂膀庇护着彝乡儿女。
披毡的动态变化是山之意象的点睛之笔,开合之间,时而化作山巅的流云,时而凝为山谷的暗影;舞者伸展遒劲的动作,复刻了大山的绵延与挺拔,举手投足间,既有山体的沉稳厚重,又有山峦相连的连贯气势。二者相互呼应,让阿妈与大山的形象彼此交融,分不清是舞者在演绎阿妈,还是在描摹大山。
这种将母爱与地域文化结合的叙事方式,既赋予母爱的民族特色,又让其超越地域限制。无论是生长于大山还是生活在城市的观众,都能从阿妈的坚守中看到自己母亲的影子。
这种对平凡生命的歌颂,让作品具有时代意义。它提醒着观众,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不等于固执,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个用爱守护家庭的人,都是值得歌颂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母爱永恒,坚守永恒,平凡生命中的精神力量永恒。
作者简介
刘海琨,四川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评论研究中心研究员。